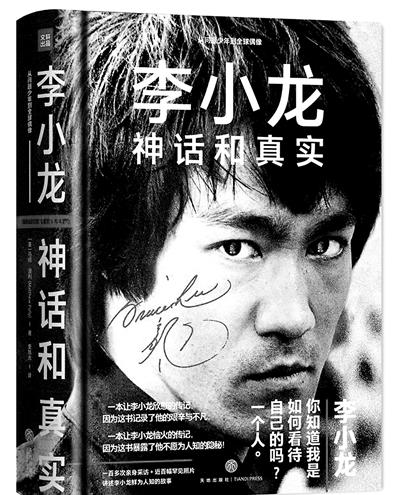
燕橋
作為李小龍的愛好者,看到這本傳記我很驚訝,為什麼馬修·波莉花了七年時間寫了一本70萬字的李小龍傳記?他的少林很忙,很多讀者都知道,就是用一種"體驗"的風格,來寫功夫筆記。一個美國人,進入少林寺體系,陌生的新鮮視野,看一切,除了"外國視角",什麼都不是,是不允許學習的。而這本李小龍傳記,體積巨大,單一資料完成2500頁,超過100萬字,作者還親自采訪了100多名認識李小龍并願意與"當事人"交談的人,做了大量的案頭準備,作者在英文世界最詳細的筆記、信件、訪談、口頭及相關著作, 到"拼貼"一個真正的李小龍。
接縫中的周長和平衡
李小龍在他的研究領域最缺乏的是類似于"喬布斯傳記"的嚴肅傳記,這就是本書的全部内容。随着葉巧的傳播,李小龍相關影視劇,又重新開啟了關于李小龍文化熱潮的流傳,李小龍在媒體上形容"人性設定",是一個混合了民族主義和體力的神話,那踢出了"東亞病夫"牌匾,赤裸的上半身,怪鳥的聲音無敵"東方巨星", 長期占據我們的大腦。為了産生先入為主的印象,李小龍讓西方人重新認識東方,功夫是民族自信的一部分,東方打敗西方,這是一個刻闆的神話。這種"純粹的民族主義"一攬子計劃并沒有真正反映當時亞洲行為者的困境。
李小龍自從成為私人教練以來,一直在說服美國演員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參加他的武俠電影,這是當時亞洲面孔可以投資的唯一途徑。麥奎因一直在躲閃,在他看來,李小龍隻是一個高成本的教練,被迫匆匆忙忙,他向李小龍展示了"面對現實......我不會讓你踩到我。
1969年1月7日,李安寫了《我的明确目标》,上面寫着:"我,李小龍,将成為美國收入最高的東方巨星。作為回報,我将作為演員提供最激動人心的表演和最佳表演。從1970年開始,我将享譽全球,到1980年底,我将擁有1000萬美元。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實作内心的和諧與幸福。
顯然,在史蒂夫·麥奎因(Steve McQueen)拒絕後,這部電影是帶着羞辱寫的,西方制片人沒有看到帶有英國口音的東方面孔,他的職業生涯停滞不前,而香港的電影業在關鍵時刻給了李小龍一個緩沖區,就像飛地一樣。
香港媒體曾經用過一個術語來形容李小龍是"太平洋的終極中間人"(對西化中國人的模仿),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術語。中間商也意味着戰略。在《唐山老大哥》上映之前,李安并不急于與華納簽約,"如果票房賣完,他可以用它來提升自己的議價籌碼。李某與餘文懷合作,謊稱尋找易福的聯系人,同時釋出消息稱肖想挖高薪的人,以增加合作夥伴的危機感,獲得最大的籌碼。"當派拉蒙在香港給我打電話時,我的香港制片人認為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明星,是以我的聲譽肯定增加了兩倍,"李在香港告訴記者。"中間人是一種政策,一個既縱向又跨領域的角色,一直圍繞着東方(香港)和西方(好萊塢),李宇善于利用香港票房來增加價值,赢回好萊塢,重新獲得人氣。
在之前的傳記中,"東方的勝利"總是被宣布得太快,忽視了接縫中的圓周和平衡以及亞洲身份和職業突破的困境。這本傳記的想法是蛇形的,隻把人放進娛樂市場的制作機制中,在東西方中間,如何讓雙方都需要,就像擺渡人一樣。加藤在《綠蜂人》中,按照早期的設定,是一個熟悉的空手道東方面孔,然而,他隻是"使用的主角",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小龍扮演的隻是"西方對東方的想象"。他迎合了一個機會,創造了一部全新的電影。
入侵者的動作美學
在錄像帶時代,我反複用慢動作看李小龍的動作片,不能不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李的武俠動作,再是香港流行的龍虎武俠師作為代表的"武打"是很不一樣的,甚至同一部電影的"對手"也大相徑庭,就像是兩套動作系統拼湊在一起, 就像兩個世界。李小龍的動作更加流暢迅速,接近真正的戰鬥,并伴有大量的高踢、連環踢、空高踢等等,對手戲打誇張,體操一般。李小龍對當時香港粵劇中的傳統打鬥不屑一顧,他說:"每個人都在打架......為什麼他們的打鬥風格一模一樣",他要求要接近"真搏鬥",拳頭對肉,這與電影動作指導相沖突,在《唐山老大哥》中,動作向導韓英傑想用粵劇舞台動作、蹦床和傳統套法打鬥,而李小龍"拳打腳踢得太狠......我的臉被他的一腳踢傷了。
李是外界的闖入者,重新定義規則,他不僅想成為"演員",他還把自己看作制片人,這反過來又與導演羅威的控制産生了不可調和的沖突,那種港式松散的導演的集團管理,被李小龍認為不夠專業, 兩個人的概念甚至價值之火,甚至後來出現近乎"刀"的不愉快事件。排除私人不滿,更根本的是,這種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李想要收回"圖像控制",并希望在作家,攝影,導演,布景和所有細節中擁有發言權,以便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為了獲得控制權,他上上施壓,要求換導演或者幹脆幹自己導演,讓動作向導不要幹預太多,為了達到動作,不得不和龍虎武俠師打底,"他會和他們一起吃午飯,用黃色的笑話來結束關系, 拒絕享受特殊待遇",走群衆路線,籠中人。其實,如果沒有這種"野戰政治"的勝利,我們今天看到的李小龍動作片,遠非那麼個人化,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大腦的理想武俠電影來實作。
即使在今天,李小龍的許多電影創意都很先進,甚至不能簡單地歸類為"無中生有的電影"。在那個時代流行的"複仇模式"電影中,暴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敵人被實體摧毀,沖突被化解,暴力是本能的,甚至是内在的體積。而李演繹了"無聲笛",英雄出發去尋找武俠聖經,必須通過三次考驗,分别象征着自我、愛情和死亡,他的向導是一個名叫阿薩姆(潛意識的象征)的盲人,在結局中,雖然英雄發現了秘密,但在李小龍的修改版中,他轉向了秘密, "慢慢地,英雄撿起了秘密,一頁一頁,上面的空白。這時,他翻到最後一頁,裡面有一面鏡子,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這有點像禅宗的"磨磚鏡"的氣味,故事指向"虛無主義",暴力甚至自我意識的障礙,沉默的笛子,如何傾聽,都在你身上。
這樣的打法,由于缺乏市場和過度的腦力燃燒,生産者往往不确定,不被青睐。然而,從美學上講,它們往往是超驗的和橫向的,與那個時代相去甚遠。我們看到的那個癡迷于武力、血迹斑斑、肌肉斑斓的李小龍隻是膚淺的,大衆更願意了解一個"雕刻"的、象征性的或神化的李小龍,更扁平、更容易傳播。
死于中暑?猝死之謎有了新的解決方案
關于李小龍猝死的奧秘,有各種各樣的記載。這本書的作者提供了一個相當新穎的"解釋":死于中暑。
由于布魯森的屍體解剖是由"腦水腫"引起的,香港的神經外科醫生将李小龍的昏厥歸咎于大麻,但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它與死亡有關。除了李小龍的一生,在兩份昂貴的人壽保險上,吸食大麻可能是一種免賠條件,是以在審判記錄中,當事人盡量避免确認"吸食大麻",這導緻更多的媒體猜測,"死因"與多方利益和博弈有關。
作者提出了一個新的推理:"中暑是年輕健康男性突然昏厥,癫痫發作甚至死亡的最常見原因。在年輕運動員和士兵中,死于中暑的機率為3%至5%,在運動員中最常見的緻命疾病中排名第三,在夏季最熱的月份上升到第一位。
李小龍臨死前的身體表現,"呼吸困難,顫抖,全身濕透了汗水",全都符合中暑的症狀,"拍攝《龍拼》時,他承受的壓力太大,身心疲憊。在過去的兩個月裡,他已經減掉了18磅,他的體脂已經減少到最低限度。在他暈倒的前一個月,他剛剛接受了手術切除腋下汗腺,......沒有這些汗腺,他的身體散熱能力就會降低。作者認為,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醫生對中暑的了解比現在要有限得多,是以他們誤以為是高燒,最終延誤了治療。由于當時的醫療記錄已不複存在,是以我們沒有深度可以探索。
總之,這本李小龍傳記沒有武斷,也沒有繼續"造神",它用各種曆史資料來支援,盡可能地給我們帶來"真實版的李小龍"。我們不應該停留在偶像或符号的光環中,而是忽略了真正的混凝土,即有血有肉,有品格和弱點的李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