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考古火出了圈,從聯考狀元立志進北大考古系,到火遍天際的《國家寶藏》和《如果國寶會說話》,再到故宮文創的崛起,文物一下子走入了大衆視野,走進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們真的了解文物的重要性嗎?我們真的知道怎樣通過一件文物解讀它背後的政治制度、思想潮流和曆史變化嗎?《文物裡的早期中國》解答了這些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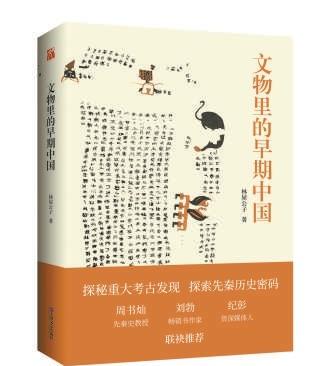
《文物裡的早期中國》 林屋公子 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林屋公子自謙稱《文物裡的早期中國》為一本從先秦秦漢文物中讀上古史的“小冊子”。實際上,這本書通過34件很有代表性的文物,如郭店楚簡、清華簡、吳鈎越劍、馬王堆帛書、三星堆銅人,重新解讀漢代之前我們自以為熟知的神話與“信史”。
按照顧颉剛先生的論斷,對古史的研究經常出現“古史層累”的現象,就像在考古挖掘中後一個時代的遺迹一定覆寫于前一個時代之上,導緻時代越久遠的遺迹越被壓得失真了。在早期中國史的研究中,出土文物的地位尤為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是漢代之前史料的缺乏,兼之後世紛纭繁雜的解讀,此時文物能最直接地還原當時曆史的真實面貌,與史籍記載相印證,有助于讀者辨識記載的真僞。随着時代的推移,尤其到唐宋之後,文字書寫和記錄方式幾乎覆寫了社會生活的邊邊角角,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
林屋正是抓住了漢代之前,由于史料缺乏加之“古史層累”造成的“信史不信”的痛點寫了這本書,選取了帶有文字的文物,這樣的文物往往用于祭祀、祝禱等大型活動,本身就傳達了很多資訊,訴說了一段完整的故事,同時可以與史籍相印證,更容易展開與之相關的時代、人物、事件的講述。
比如其中有幾段有趣的故事:黃帝存在嗎?堯舜的傳位真的是禅讓嗎?
我們是炎黃子孫的記憶刻在骨血裡,以至于不再質疑,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作者林屋公子從陳侯因齊敦上的銘文“紹緟高祖黃帝”入手,開始一步步梳理了黃帝的字義與來源,從商代開始找尋黃帝的痕迹,發現直到春秋時期,即使在《詩經·商頌·玄鳥》和《大雅·民生》兩段分别講商周人族源的史詩中都無黃帝的痕迹,作者一路往後,在《史記·封禅書》和《五帝本紀》中關于五帝源起的回溯才定位到,黃帝的概念大概形成在戰國時代,而上古諸帝王在此時整合離不開當時秦帝國政治統一、“華夏”自我認同明确化的社會情境,身處其時的“陳侯因齊敦”記錄的也正是這樣一個“攀附”的故事,“炎黃子孫”随着政治地理邊緣的擴大,漸漸成為共同文化心理認同的一塊基石。
書中同樣讨論了古史上很有争議的禅讓話題,堯舜禹之間是禅讓還是篡奪?權力的和平交接究竟是不是後人的美化?為了解答這個疑問,作者選取了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紀山鎮郭家店的楚簡、上博簡和清華簡中的篇章,開啟了堯舜禅讓的探秘。這些成于戰國中期的竹簡,無一例外記錄了禅讓這段令人稱頌的佳話,反映的基本是當時普遍流行的思潮,與正史中的記錄幾乎可以一一印證,唯與《竹書紀年》的記載大相徑庭。再從傳世的《論語》《墨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孟子》等文獻中對禅讓的讨論,大緻能推斷出,禅讓學說應該在前314年燕王哙禅讓失敗開始才遭到質疑。
跟随作者的探索能發現,很多後世的扭曲和重建,都源于當時的政治需求和思想潮流。比如原本出身貴族的管仲,卻被後世塑造成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細究當時的背景,會發現當時恰恰出于貴族政治解體的時代。再如《封神演義》中流傳甚廣的姜太公古稀之年才拜相輔佐武王伐纣,從頭到尾不過是個勵志故事,當從文物和文獻中出發仔細研究才得知,太公望伐纣時正值壯年。而太公望從人變作神化的異士,與道教的興盛脫不開幹系。
在論述之間,作者總會穿插自己對待曆史的看法。如在談論“炎黃子孫”問題上,對周邊民族的“華化”與文化的自我認同上,一言直指要害,“在華夏國家與民族産生的過程中,他們的形象被按照共同文化心理需要進行了塑造,華夏民族從形成之時其就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第三章《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中說,“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别的标準,這個标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别之明證。”這種觀念給古代的中國人一種彈性空間,不至于在外族侵入的時候有迷失感,相反,甚至有了一種同化它族或非夏文明的文化自信。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當偏弱的文明向中原靠近時,也多借口與華夏文明靠攏,比如越國等周邊四夷,借用華夏的始祖、神話、傳說,将自己歸于中原文明的主流體系之下。由文物的叙述上升到“何為中國”的文化溯源,在書中并非孤例。如他所說,我們并不是要通過文物推翻曆史,而是要打破傳世文獻的記載,多結合考古發現成果,重新思考很多曆史問題。
借由對上古神秘面紗的揭開,帶給我們深思的實際上是一場自我認知之旅。(責編: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