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荀子的“解蔽”之方與“治氣養心”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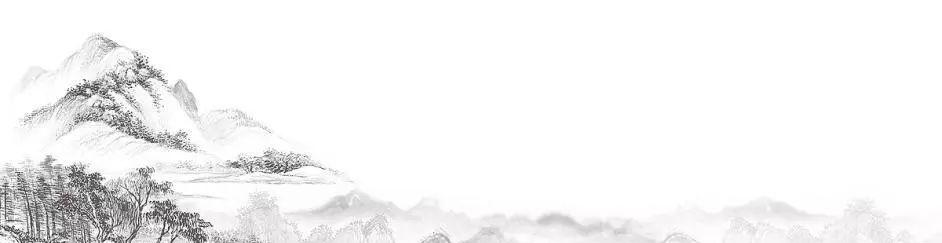
作者簡介丨匡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哲學。
原文載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04期。
摘要
在以“養心”為目标的“心術”當中,荀子所看重的,首先是心能“知道”與如何“知道”。這對等于獲得理智德性的精神修煉,而荀子對這一方面的精神修煉的見解,可以分解為前後兩個環節:先“解蔽”,其次達到“大清明”。除了與理智德性的修養有關的“心術”之外,不曾放棄對儒家傳統道德德性之追求的荀子,同樣考慮到了與之有關的精神修煉技術,即那些與“氣”有關的修養方式。對于後一種修養方式的思考,荀子稱之為“治氣養心”,且相關思考,主要是從矯正性的角度着眼。荀子所謂“治氣養心”之術是以改變自己為目标的學習、修身手段,這些技術與荀子所提倡的其他諸如經典學習與禮樂訓練一起,構成了他所謂“以美其身”的“君子之學”。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學者傾向将荀子所關注的心靈的思知層面上的内容與孟子所言的心靈的先天道德能力對立起來,視為這兩位儒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如徐複觀便判定:“孟子所把握的心,主要是在心的道德性的一面;而荀子則在心的認識性的一面;這是孟荀的大分水嶺。”[1]146牟宗三也有類似的評價:“荀子隻認識人之動物性,而于人與禽獸之區以别之真性則不複識。此處虛脫,人性遂成漆黑一團。然荀子畢竟未順動物性而滾下去以成虛無主義。他于‘動物性之自然’一層外,又見到有高一層者在。此層即心(天君)。故荀子于動物性處翻上來而以心治性。惟其所謂心非孟子‘由心見性’之心。孟子之心乃‘道德的天心’,而荀子于心則隻認識其思辨之用,故其心是‘認識的心’,非道德的心也;是智的,非仁義禮智合一之心也。可總之曰以智識心,不以仁識心也。”[2]224這些評價,隻看到了荀孟之間的差別,卻沒有足夠強調荀子所言思知與道德實踐之間的連續性。前一方面的内容早為人所熟知,而從後一方面來說,無論是荀子對于人思知能力的培養,還是孟子對于人道德能力的發展,均服務于人格塑造和德性養成——更精确地說,荀子給後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更關注理智德性的獲得,而孟子則更關注道德德性的獲得。1但是作為儒家的荀子,在追求理智德性的時候絕對不會放棄對于道德德性的追求,這正如荀子既有對于心之思知的訓練,也有對于“治氣養心”的關懷,甚至我們可以從荀子本人的著作中推斷,他應該已經看到了上述兩種精神修煉技術之間的連續性,行道首先要知道,倫理實踐離不開理智的指引。此外值得說明的是,雖然荀子在對于人心的看法方面與孟子存在巨大差異,但如果他從自己心有思知能力的立場再前進一步,如蘇格拉底所暗示的那樣,主張心靈同樣具備某些先天的知識,那麼他與孟子之間立場上的差異就會變得非常細微了,先天的道德能力與先天的道德知識之間的差别,僅僅在于實踐上的側重略有不同而已。當然荀子雖重視心知的能力,但也并未像古希臘人那樣給予人的心智過多的信任,而上述可能性也未曾出現在儒家思想中。
一、心何以“知道”
從以上角度來看,在以“養心”為目标的“心術”當中,荀子所看重的,無疑首先乃是心能“知道”與如何“知道”。荀子有言:“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暫時不考慮“心術之患”的特殊說法,荀子所知之道,當然還是判别是否的标準:“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荀子·解蔽》)荀子繼續主張“人何以知道?”(《荀子·解蔽》)的關鍵在于“心”,這個有思知能力的人心,因思而“知道”,進而遵循“道”,并據此改變自己的方式便是“僞”:“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僞。”(《荀子·正名》)荀子還認為人格中美好的品質也是被創造出來的,所謂“善者僞”(《荀子·性惡》),這種顯然超出知識意義之上的價值創造首先也取決人心的思知能力。既然人心是一切問題的起點,荀子便有必要對其加以更細緻的分析:“生之是以然者,謂之性。……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荀子·正名》)這裡出現的“性”“情”“慮”,是從三個方面對人心加以總括性的說明,“性”所表征的是心的生命禀賦的基底,在此基底上,心所具有的第一方面内容則是情感、情緒意義上的“情”,而對于“情”的進一步處理,便産生了第二方面,即思知層面上的内容“慮”。荀子認為思慮與情有關,顯然與《性自命出》中關于“情思”的種種說法有關。稍後荀子繼續将對心的分析擴充到“欲”或者說欲望上面:“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荀子·正名》)在荀子的這個分析心的觀念譜系中,“性”“情”“慮”與“欲”,均不脫離生命禀賦的先天性,比較重要的看法則在于,在這些先天的、價值無涉的内容中,有的任其發展便會導向負面效果——比如“情”與“欲”,而其他的則是引導人趨向“道”的積極因素——比如“慮”。心之思慮,也被荀子稱為“征知”:“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征知。”(《荀子·正名》)荀子在這裡将“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和“說”“故”都和心聯系在一起,利用對後面這些本存在于論辯環節中内容的了解,繼續擴張了心之思知能力的範圍。
對于擁有上述能力的人心,荀子依然主張其對人身體的支配:“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這個定位近與稷下黃老學之《管子》“四篇”中“心體君位”的思想有關,遠與《國語》中“正七體以役心”的說法相先後,而從儒家内容的思想傳承來看,則與郭店簡書中的内容密切相連。對此荀子在《天論》中也有類似表達:“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統五官,夫是之謂天君。”人心的能思慮的方面,對于人心情、欲的方面還有絕對的控制能力,荀子舉生死為例說明了“治亂在于心之所可”的道理:“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荀子·正名》)這裡荀子提出的最為重要的觀念,便是文中所謂“理”,心的思慮活動,正是因為合乎理才相對于“欲”位于更高的“止之”“使之”的地位。理在荀子這裡歸并于道的範疇之下,心能“中理”,不外還是心能“知道”的意思。
荀子對于論證活動本身給予高度關注,而這方面内容當然也與心之思知能力密不可分。不但前文涉及的“說”“故”,包括“辨”“辭”之類的内容也都與心靈有關:“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于道,說合于心,辭合于說。”(《荀子·正名》)這裡暫不對荀子所使用的用來表述論證諸環節的術語加以分辨,重要的是荀子将其視為“心合于道”的标志,這等于是為“知道”設立了可以實際把握的客觀标準。荀子對于心之思知層面内容的思考,在儒家學者中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細緻。
荀子思考中更重要的内容在于心如何“知道”,這對等于獲得理智德性的精神修煉,而荀子對這一方面的精神修煉的見解,可以分解為前後兩個環節:先“解蔽”,其次達到“大清明”。曾有論者從傳統上認識論的角度總結先秦諸子對心的思考:“春秋末期到戰國早期的認識論,關注的主要是知識的來源和求知的方法、途徑等問題。……人們着重探讨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妨礙正确認識的因素是什麼,二是認識主體——‘心’處于什麼樣的狀态才能獲得正确認識。”[3]105可以說這兩方面内容,在荀子的思想中都有明确反映。就“妨礙正确認識的因素”而言,白奚認為在先秦的思想譜系中,哲人們有大量可從此角度加以了解的看法:“在妨礙正确認識的因素(即認識為什麼會陷入錯誤)這個問題上,……如慎到所謂‘建己之患’與‘用智之累’,宋钘所謂‘宥’,莊子所謂‘成心’,《管子》所謂‘過在自用’和‘去智與故’,韓非所謂‘前識’,荀子所謂‘蔽’,《呂氏春秋》所謂‘尤’與‘囿’等。”[3]106專就荀子而言,問題自然便集中在應“解”之“蔽”,也就是荀子所謂:“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對于何以會出現“蔽于一曲”之“患”,徐複觀以為是由于“心的認識力之不可信賴”:“《解蔽》篇說‘聖人知心術之患’,術是田間小徑,心術是指心向外活動之通路而言。心術之患,正指的是心的認識力之不可信賴。”[1]148這裡徐氏将“心術”這個術語所指的對象看窄了,荀子所要說明的,乃是整個精神修煉過程中都可能出現問題,隻是這些問題首先會表現在思知當中,也就是懷疑人心有“蔽”。但這些“蔽”,并不意味着人心本身的思知能力并不可靠,對于人身之“君”“主”,荀子實際上并未表現出任何的不信任,甚至随後指此心:“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從上述言論可以推斷,在荀子看來,心靈完全是自我做主的,至于影響其正确判斷的,并不是心靈本身的天然缺陷,隻是由于受到了蒙“蔽”,而這些“蔽”一旦解除,心本身則呈現出“大清明”的狀态。
荀子在《解蔽》開篇不久便為我們列舉了“為蔽”的十種原因:“故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而上述這些原因除“欲”“惡”之外,顯然不能被簡單歸于心靈思知能力的缺陷,更多則與經驗上的差異有關,用荀子自己的話說,“蔽”的直接來源就是“萬物異”的客觀狀況,而人心隻要面對這些“異”便不免受到負面影響:“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荀子·解蔽》)如果我們有能力排除上述妨礙正确思考的因素,那麼心便能“知道”,而這也就解決了“如何才能獲得正确認識”的問題。有論者以為:“戰國中後期的思想家們的目光都集中在認識的主體——‘心’上,都認為‘心’處于某種特定的理想狀态便能獲得最高的修養,也就能獲得正确的認識。如莊子所謂‘心齋’,孟子所謂‘存心’‘養心’,《管子》所謂‘心處其道’‘虛素’,荀子所謂心之‘大清明’‘虛壹而靜’等。”[3]107上述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不同性質的“心術”混淆在了一起,抛開莊子、《管子》不談,孟子所謂“存心”“養心”與荀子所謂“大清明”“虛壹而靜”相比,強調的乃是不同類型的精神修煉工夫,前者專注于道德德性的獲得,與“氣”的修養相關,而後者專注于理智德性的獲得,方與“思”的修養相關。
如果說“解蔽”隻是荀子眼中與思知有關的精神修煉的第一個環節,那麼随後的環節便是心靈在擺脫“蔽”的影響後達到“大清明”或“虛壹而靜”的狀态,而後一種狀态既是對“蔽”的克服,也是對心靈先天能力的呈現。荀子在讨論過種種之“蔽”以及相關的例子之後,從三個方面将這些因素總結為“臧”“兩”和“動”:“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荀子·解蔽》)将這三方面負面因素分别加以克服,便達到“虛壹而靜”的理想狀态:“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荀子·解蔽》)
就荀子所謂“臧”“兩”“動”而言,“臧”之所指乃是人心中因原有知識而帶來的主觀性,而首先隻有排除這種主觀性使心“虛”才是正确的認識“道”的方式。至于“兩”指的則是不同的意見,前面提到的荀子認為“為蔽”的十種原因可歸結為一個“異”字,而此“異”實際上也就是所謂“兩”:“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荀子·解蔽》)我們的目标便在于,設法避免其互相間的沖突與沖突而讓兩種不同的意見達到統一之“壹”。最後所謂“動”,指的則是各種幻覺或錯誤資訊的不良影響,設法避免上述錯覺而“靜”心,對于“求道”而言也是必須的。對于心靈圍繞上述三方面所展開的活動,早有杜國庠繼郭沫若之後注意到荀子相關思想與以《管子》“四篇”為中心的稷下黃老學之間的關系。從學術史的角度看,荀子的思想會與稷下黃老學發生聯系并不奇怪——稷下學宮的存在将他們聯系在一起,具體就其思想關聯方面的細節而言,杜國庠曾從傳統上認識論的角度詳細讨論了荀子所謂的“虛壹而靜”。[4]134-157“虛”向來是一個道家的說法,向上很容易回溯到《老子》“緻虛極,守靜笃”的言語,而《管子·心術上》中也有“虛其欲,神将入舍”的說法,杜文認為此“虛”與宋子所講的“情欲寡少”有關——這大概是受到郭沫若對于《管子》“四篇”作者不太可靠的考證影響的錯誤結論,不過他卻正确指出,與上述思想相對,荀子并不主張單純的“去欲”,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不以所已臧害其所将受”(《荀子·解蔽》)表示的是對于人心主觀性的拒絕。至于“壹”的問題,杜文注意到《管子》“四篇”中所謂的“一意專心”之類的說法重點在于養生,而荀子則與此相反,完全是在思知的意義上主張統一不同的觀點,“不以夫一害此一”(《荀子·解蔽》),但卻并不了解,荀子所強調的思知上的統一,仍然具有與《管子》相類似的精神修煉意義。同樣,杜文也發現對于“靜”的看法荀子也大不同于《管子》,《管子》“四篇”旨在以靜制動,以靜養心,如《管子·内業》所謂:“凡道無所,善心安處,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心能執靜,道将自定。”荀子的主張“不以夢劇亂知”(《荀子·解蔽》),卻是在提倡一種積極意義上的“靜”。總之,杜文認為荀子強調心積極的認識作用,而《管子》“四篇”則完全停留在虛靜無為的道家立場上。抛開這種立場上的差異,荀子對于“虛”“壹”“靜”的了解,都帶有主動消除主觀性、統一不同觀點和擺脫錯覺幹擾的積極意義,而他對上述内容的看法卻并未停留在傳統的認識論層面而與修身有關,這些與思知有關的精神修煉,仍然是以德性的獲得、人格的塑造和人自身的改變為目标的。
在荀子看來,如果我們的認知心能達到上述杜絕“臧”“兩”“動”之影響的狀态,便是達到了“知道”所必須的“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于室而見四海,處于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荀子·解蔽》)荀子對于這樣的無蔽之“大人”予以了充分的信任,而此等人也是以由普通意義上的“人心”而進于“道心”了。荀子極力贊美内心掌握“道”之精微者,對于這樣的人他在《解蔽》的後文還以莊子般的口吻稱之為“至人”。當然這樣的“至人”絕非翺翔于莫可名狀的虛靜狀态的道家人物,在荀子這裡,他仍然是立足于仁德的儒家聖人,雖然此聖人因為對于外在的道的依賴而不免顯示出一些“無為”“無強”的道家風格:“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強也。”(《荀子·解蔽》)
二、從養生到修身
荀子雖然最為重視心靈的思知能力與相應的精神修煉,但他卻并未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嚴格來說,這個層次的精神修煉,可能隻是荀子所設想的改變自己的努力的起始,而在圍繞思知展開的修養之後,還有更進一步的後續工作。除了這些與理智德性的修養有關的“心術”之外,不曾放棄對儒家傳統道德德性之追求的荀子,同樣考慮到了與道德德性有關的精神修煉技術,即那些與“氣”有關的修養方式。對于後一種修養方式的思考,荀子稱之為“治氣養心”。
在讨論“治氣養心”之前,荀子先提出了“修身自名”的問題,并将其與“治氣養生”對舉,統稱之為“扁善之度”: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于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态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荀子·修身》)
在這個“扁善之度”的題目下面,荀子首先對比了兩類不同追求的“修身”:一是道家式的,以追求“長生久視”為目标的“治氣養生”,這種“修身”的目的與早先的老子一樣,重點在于效仿彭祖長久儲存肉體生命;一是儒家式的,以追求“禮信”為目标的“修身自名”,這種修身的目标則與先前的孔子一樣,重點在于追求德性。荀子将前一種“修身”完全納入到後一種修身内部,這等于是取消了其獨立的地位與意義。
在上述言論中,荀子實際上提出了兩個論點。首先指出了修身活動的用意所在,在與“氣”有關的修煉活動中,排除了單純以身體儲存為目标的“治氣養生”;其次不拘于“心術”範圍,對修身活動做出了一個整體的說明,并分析了修身實踐展開的三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這裡真正強調的乃是被他作為所有修身活動總原則的“禮”,而非作為某一種修身技術或進路的“禮”——荀子這裡所謂“禮”,與他所謂“道”是一緻的,是後者的具體規範化,覆寫了個人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其意涵超出了早期儒家“為己之學”問題域[5]内禮樂訓練進路意義上的“禮”。
荀子在這裡指出的修身實踐所得以開展的三個方面,分别是“血氣、志意、知慮”這樣的身體、生命或者說“性”的方面,與“食飲、衣服、居處”有關的個人與公共生活方面,以及與人的容貌姿态等有關的身體訓練方面。其中第一方面與道家“養氣”意在“長生久視”的傳統有關,而後兩方面則反映着儒家修身實踐的特色,其内容遠可回溯到《論語·鄉黨》中的各種記載,近則與孟子“踐形”的說法有關,儒家從來都認為,人的内在德性應該有相應的外在反映。最終的修養原則,可被歸結為以禮修身——荀子總結說,禮所代表的内容,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群體,都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在荀子上述對于“修身自名”思考中,他首先對身體層面的“養生”有所關照,而這一點或許與他對于直接與生命禀賦相關的“欲”和“情”等方面内容的比較正面的看法有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上述身體層面的項目都是修養的對象,但這方面内容卻絕對不是他思考的核心。儒家傳統中從來都不重視獨立的以肉體生命為對象的“養生”話題,而荀子也不例外,在他的思想裡,這方面内容總是被歸結到“禮義”的話題之下的:“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是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荀子·強國》)換言之,對身體層面之“養生”的要求,乃是荀子所強調的儒家所主張的“禮義”的題中應有之意: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别。曷謂别?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是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是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是以養目也;和鸾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是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是以養信也;寝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是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是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是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是以養财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是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是以養情也!(《荀子·禮論》)
禮義要求我們對于身體層面的“養生”有所關照,而這方面的重點落在不同身份、狀态的人應該享受不同的生活待遇上面,至于荀子在談“扁善之度”的時候,從修身技術角度之是以要關心衣食住行、容貌姿态這樣的内容,肯定也與上述考慮有關——禮的具體要求,便包含了對不同的人應該怎樣穿衣服、怎樣說話行事等方面内容的規定。從這個角度講,身體層面的“養生”的關鍵在于“适度”照管身體,否則“養生”的效果便會适得其反。荀子在《樂論》末尾處,便将“養生無度”視為“亂世之征”,他在其他地方還明确說到無度之“縱養”根本就是有害的:
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荀子·正名》)
究上述“養生”的負面效果的緣由,當然是因為上述“縱養”未能遵循禮義,而變得毫無正面意義。至于關乎衣服飲食和容貌姿态的修養,簡單地說就是有關活動必須合乎禮義的要求,這些既涉及私人與公共生活,也與身體訓練有關的實踐,因統一于“禮”而最終歸結到人格價值的修養上面去。
荀子在“扁善之度”的話題下面,所關注的最重要内容當然仍是儒家傳統的德性尋求與人格塑造,而其對修身實踐的概說,從技術上講則早已超出了“心術”層次的内容,但是無論在追求價值的過程中運用了什麼樣的修身技術,對于荀子而言,在早期儒家主張“心術為主”的意義上,心在所言這些修養活動中均不會缺席:
心憂恐,則口銜刍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荀子·正名》)
相反: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局室、蘆簾、稿蓐、敝機筵,而可以養形。(《荀子·正名》)
之是以會出現上述狀況,原因便在于相對身體而居于支配地位的“心”。
三、“治氣養心”之術與矯正性修煉
既然在“修身自名”的題目下面,無論将牽扯到何種類型與層次的修身技術,“心術為主”的立場也不會受到動搖,那麼荀子緊接着在對上述話題進行全局性思考之後,便迅速轉向更為專門的精神修煉範圍内的“治氣養心”之術,便是非常自然的。從論證政策上說,荀子顯然是在上下文中将其與前面所謂“治氣養生”之術加以對照,并以後者的不完備來凸顯前者重要性: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驽散,則刦之以師友;怠慢剽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悫,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荀子·修身》)
但荀子所談到“治氣養心”之術,如将其視為對狹義的、精神修煉意義上的“心術”的一個具體說明,則包含了一些必須加以說明的特殊問題。
荀子所謂“治氣養心”涉及對人的心态九個方面的調理,其具體内容大多沒有被哲人們詳細地考慮到,荀子在這裡對于人所可能表現出的驕傲、陰險、粗暴、詭詐、狹隘、卑鄙、懶惰、懈怠和愚蠢頑固均提出了相應的治理對策,但如果他的對策同樣被視為與氣有關的精神修煉技術,那麼與以往的儒家思想相比,至少出現了三個明顯的差別。
第一個差別在于對氣這個觀念的把握。從荀子本人對“氣”的定位來看,他對這個觀念把握實際上包含着内在的沖突,一方面似乎視其為春秋時代為人們所了解的“血氣”——此“血氣”與荀子前面談到“扁善之度”時所用的“血氣”一樣,應該是屬于身體層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從荀子将“血氣”與随後言及的一系列精神性内容并列的角度來看,他似乎又将其視為精神性的内容。以往《管子》中曾多次提及“血氣”這個觀念,它作為驅動生命的自然力量,本停留在質料性質的“氣”的水準,如《水地》所謂“水者,地之血氣”,而《内業》所謂“四體既正,血氣既靜”,大概還是表達了這種意義。這種身體意義上的“血氣”與氣息之氣一樣,在統一于生命現象的情況下,可以逐漸與精神性的活動發生聯系,而最終在道家系統内過渡到與心靈密切相關的精氣。由此氣也被視為精神層面的内容,而相關的修煉,也已經出現在精神修煉的範圍内。這一點在《管子》“四篇”所反映的稷下黃老學思想中已經有所表現,而在儒家譜系内,從一開始引入氣與相應的修煉思想,所看重的便都是超出身體之上的精神層面上的氣——無論《五行》中的“德氣”說,還是《孟子》中的“浩然之氣”,都應作如此看待。也就是說,在稷下黃老學的某些部分和全部早期儒家的思想當中,血氣與精神性的氣的區分非常清楚,但在荀子這裡,從他對“血氣”的前後用法來看,上述區分卻顯得有些含混。會出現這種狀況,或者說荀子堅持讨論“血氣”,并将其與種種精神性内容并列,可能與他一貫強調人的生理層面的生命禀賦有關,也可能與他對以往儒家圍繞“氣”展開的種種言說的“隐約”有所不滿有關,但從早期儒家的整體思想狀況而言,荀子論氣的方式,卻反而顯得有欠流暢。
第二個差別在于對與氣有關的修煉方向的把握。早期儒家以往與精神性的氣有關的修煉,清晰地指向道德德性的獲得,而這一特色在荀子這裡也完全無從尋覓。荀子談到的“治氣養心”的九個方面,包含了各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内容在内:其中既有關乎理智德性的成分,如“知慮”“思索”,也有關乎道德德性的成分,如“勇敢”,還提到了諸如“師友”這樣的德性典範。如果将這些内容都與氣的修煉聯系起來,則以往儒家與道德德性有關的修煉指向,便完全不見蹤影了。從孔孟之間儒者較早時引入以“内外”為根據的新的德目的分類标準開始,孔子本人确立的對于理智德性與道德德性的劃分就開始變得模糊起來,而上述劃分因被遮蔽而最終退出曆史舞台的推手,則是孟子。早期儒家發展到荀子這裡,上述理智德性與道德德性之間的劃分,可能已經被完全遺忘,而他隻是無意識地遵循儒家一貫的在精神修煉領域内的工夫區分,分别談論着與思知有關的“解蔽”工夫和與氣有關的“治氣養心”工夫,但對于後一類工夫的特殊針對性卻已經沒有了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從《荀子》中《解蔽》的文本和《不苟》中關于“誠”的言論來看,推測荀子最重視與“思”有關的精神修煉工夫,并認為這種工夫對其他德性的獲得具有毫無疑問的優先性,大約既不違背荀子的本意,也不與上述不同類型德性間的邏輯關系相沖突。更有意思的是,荀子在上述方面與孟子之間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實際上在并不了解理智德性與道德德性的區分的基礎上,仍然都遵循了相應的精神修煉工夫方面的分别,隻是前者更強調與“思”有關的工夫,而後者更重視與“氣”有關的修養。
第三個差別在于對修養的整體方向的把握,而這個差別甚至并不僅僅局限于“治氣養心”的範圍之内。以往儒家在讨論與氣相關的工夫時,在将氣作為德性實作的動力性因素的意義上,對于有關實踐的說明總是積極的、建設性的,而荀子這裡提到的修煉技術,則完全是從消極的、矯正性的角度着眼。在以往早期儒家的“心術”領域,實際上一向存在一類以消滅精神活動中的不良傾向為目标的修煉,如已經探讨過的《大學》之“正心”、孟子之言“寡欲”和荀子之言“解蔽”都是從這種矯正性的角度出發的精神修煉工夫。這一方向的思考仍然可以回溯至孔子本人,無論“克己”的教導,還是所謂“子絕四”的主張:“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都是要我們努力去消除一些有不良傾向的内心活動對人格完善的負面影響。但是,這類型的消極的精神修煉實踐,以往似乎被視為相對獨立的活動,而未将其與“思”或“氣”直接聯系起來,到了荀子這裡,則不但将其與氣的修養相聯系,也如前文所未及言明的那樣,與思的修養相聯系。可能是出于這樣的立場,荀子在談論與氣有關修身技術時,并未用如孟子那樣的“養氣”的說法,而是用了更為嚴峻的“治氣”的說法,這個“治”字,恰與孔子以往所言“克”有異曲同工之妙。從矯正性的或者說負的方向思考精神修煉技術,應該說在荀子這裡表現得最為集中和鮮明,他的精神修煉工夫嚴格來說,都是從這個角度入手着眼的。這種思路在早期儒家中的進展,除了前文所涉及的内容之外,還曾經很明顯地留露在郭店簡書《性自命出》當中: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
簡書文本中對于“性”的塑造養成,不但曾運用“養之”“長之”這樣建設性的說法,也運用了“逆之”“厲之”這樣矯正性的說法。如果說上述正面或負面活動的治理對象還是整個人性,那麼在狹義的“心術”範圍内,《性自命出》也曾提出過一些批評性的建議:“凡用心之躁者,思為甚。用智之疾者,患為甚。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這些直接針對“用心之躁”“用智之疾”的反思,完全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後來荀子對于精神修煉技術的矯正性立場。
在早期儒家“為己之學”的全幅領域内,上述矯正性的立場也以其他的方式存在,最初《論語·陽貨》中便有對孔子所謂“六言六蔽”的記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子在這裡以籠統的方式,從反面說明了“學”對于人格塑造的重要意義,而所稱“蔽”,則正與後來荀子相呼應。《性自命出》對于修身實踐中“不應有”的行為,除了上文言及的内容之外,還有如下說法:
身欲靜而毋□,慮欲淵而毋拔,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壯而毋拔,[心]欲柔齊而泊,喜欲智而亡末,樂欲怿而有志,憂欲儉而毋惛(悶),怒欲盈而毋希,進欲遜而毋巧,退欲循而毋輕,欲皆度而毋僞。
這裡“不應有”的行為,不但涉及人心,也與“身”“行”“貌”大有關系。在《尊德義》中,與“應有”的禮樂教化相對比,還提及了一些“不應有”的教學項目:
教以禮,則民果以勁;教以樂,則民弗德争将;教以辯說,則民藝□長貴以忘;教以藝,則民野以争;教以技,則民少以吝;教以言,則民讦以寡信;教以事,則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權謀,則民淫昏,遠禮無親仁。
這也是主張從整體上将一些被認為起負面因素的内容,從修身的全部活動中排除出去。結合《性自命出》中出現的一個“剛”“柔”的說法:“剛之柱”“柔之約”,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儒家從來就是在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上提倡修身實踐,其中建設性的、積極的、正面的方法乃是“剛”的方法,而矯正性的、消極的、負面的方法,乃是“柔”的方法。從這個角度就早期儒家“為己之學”的三條進路而言,其中精神修煉與禮樂訓練可謂剛柔并濟——前者無須多言,而後者則如《論語·鄉黨》中暗示的那樣,既包括對于适當行為的訓示,也包括對于不适當行為的禁止;至于經典學習大概是偏于主“剛”的方法——孔子與其後學是絕對不會故意去“攻乎異端”的。
四、創見與傳承
對于自己所談論的“治氣養心之術”的具體對策,荀子最終從三個方面加以總結:“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這裡第一方面仍然回到荀子将“禮”視為修身總原則的觀點上,而第二、三方面内容,實際上講的是同樣的東西,荀子都是在強調學習過程中指導者與榜樣的重要性。從孔子開始,早期儒家已經提出了一種新的人倫關系次元:師生關系,而對于這方面内容荀子表現出極高的重視。對于“得師”的重要性,《荀子·修身》中言之甚明:
君子隆師而親友;
禮者、是以正身也,師者、是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雲而雲,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至于所謂“一好”,則并不簡單就是指“向善”,這裡的“好”,仍然與作為指導者和學習榜樣的師友有關,荀子有言:“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荀子·勸學》)所謂“好其人”,也就是“近其人”:“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荀子·勸學》)在荀子看來,“好人”“近人”甚至比“隆禮”還要重要,而缺少合适的人的指導,即便詩書禮樂這樣的修身方式,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是以荀子才會主張“師者、是以正禮也”,點出指導者與榜樣在修身實踐中的重要性,或者說師生關系對于德性養成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荀子所謂“一好”,指的應該是專心追随值得并應該追随的榜樣的意思。在學習榜樣與根本原則的雙重作用下,荀子所謂“治氣養心”之術才是以改變自己為目标的學習、修身手段,這些技術與荀子所提倡的其他諸如經典學習與禮樂訓練一起,構成了他所謂“以美其身”的“君子之學”(《荀子·勸學》),而荀子将其清晰地定位為“古之學者為己”的學習——這無疑是先秦最後的儒家大師對孔子所開辟的反思人之應是以及如何成就這種“應是”的一個有意識的回應,從孔子到荀子,早期儒家“為己之學”的問題域始終呈現出相對清晰的形象。
繼續就心術範圍内的修身技術而言,荀子對于先前儒者已經讨論到的某些精神修煉方法也多有涉及,比如在荀子這裡,“省”和“誠”的工夫的重要性,可能就僅次于“解蔽”和“治氣”。荀子多次強調“自省”或“内省”,如他在《修身》中談到:“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内省而外物輕矣。”在《王霸》中荀子還有“内自省”的說法。荀子對于修身工夫意義上的“自省”了解,無疑來自對孔子先行思想的繼承,并十分明确且有意識地将其置于“學”或者說“為己之學”的問題域中: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複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砺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這裡荀子“博學”而“參省”的說法,正是對孔子講求“學而思”的一個回應。至于荀子對“誠”的強調,如他“君子養心莫善于誠,緻誠則無它事矣”(《荀子·不苟》)的判斷,則一方面繼承了孔孟之間儒者的觀點,另一方面則也與自己對與“思”有關的工夫最為關注有關。徐複觀早已看出,在荀子這裡,“‘誠心守仁’,‘誠心行義’,這是從工夫上以言誠”[1]93,而這種與理智德性的獲得相關的工夫,在荀子看來還會進一步産生各種外在的效果,比如顯示于容貌、言語之中,展現在父子、君臣的關系之間。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可能存在于荀子和思想反映在郭店簡書中的那些一度從曆史上失蹤的儒者之間的傳承關系。比如荀子還談到:“仁者之思也恭,聖者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他将“仁者之思”“聖者之思”與精神修煉方法聯系起來的說法,明顯與《五行》經部中出現的“仁之思”“聖之思”這類工夫有關,乃是與前述“誠”的工夫同類,從建設性的角度出發、圍繞理智德性的獲得而展開的心術。
參考文獻
[1]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牟宗三.名家與荀子[M].台北:學生書局,1979.
[3]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争鳴[M].北京:三聯書店,1998.
[4]杜國庠.荀子從宋尹黃老學派接受了什麼?[C]//杜國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匡钊.孔子對儒家“為己之學”的奠基[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6):27-37.
注釋:
1儒家對于兩類德性的可能區分,相關讨論參見拙文《早期儒家的德目劃分》,《哲學研究》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