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旭/邁阿密大學哲學系碩士
在《電子遊戲與後殖民主義:帝國的重制》(Videogames and Postcolonialism: Empire Plays Back)一書中,作者穆克吉(Souvi Mukherjee)緻力于從人文學科的角度對電子遊戲進行分析。他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密切地關注有關性别、種族和多樣性相關的問題,但在近20年的遊戲研究中,幾乎沒有關于後殖民視角的遊戲研究。現實是,非西方地區的電子遊戲經常以批評殖民主義為主題,而像《刺客信條4:自由呐喊》和《孤島驚魂2》等西方主流遊戲,也強調了與後殖民主義相關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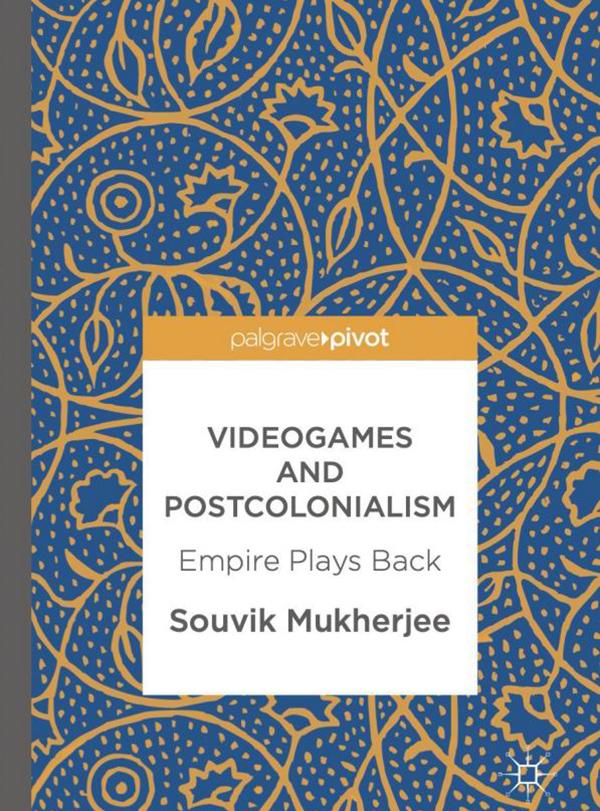
盡管有早期的嘗試,但直到過去兩年才有越來越多的遊戲研究出版物開始探索有關後殖民時代的問題。現實中豐富的研究素材與理論界對此的忽視形成強烈落差,更顯現出相關學術論著的嚴重匮乏。是以,作者認為對于電子遊戲中所展現的後殖民主義進行研究和總結非常必要,寫作這本書乃是基于一種現實的客觀要求。穆克吉的目的是進行電子遊戲和後殖民理論的連貫分析,用這本書實作對于這一缺失的彌補,推進現有的關于全球玩家(特别是非西方玩家)對待這些遊戲态度的研究,并以遊戲的視角建立對後殖民思想的學術研究。
對于如何界定後殖民主義,作者在書中指出,後殖民主義的定義往往充滿模糊性和複雜性,因為它牽連到許多不同的文化體驗和不同地區天差地别的殖民過程。殖民主義的過程和後果通常展現為“不僅從被征服的國家榨取資源、産品和财富,還重組了後者的經濟,使它們與自己的國家陷入盤根錯節的關系,是以在被殖民國家和宗主國之間存在着人力和自然資源的雙向連結,奴隸、勞工以及原材料被運輸到工業國家,而殖民地也成為歐洲商品的傾銷市場。”(Loomba 2005, 21)
讀者應該注意的是,穆克吉所使用的後殖民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并不僅意味着殖民主義的結束,也不僅是針對前殖民國家獨立後的情況。在獲得獨立的社會中,殖民時代的遺産往往依舊展現出巨大的影響,新精英的産生(無論是新制度下誕生的新階層,還是舊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新貴族)往往沒有緩和沖突,而是加劇了不平等和剝削等問題。總的來說,後殖民理論包含了一系列廣泛的議題,這些内容與昔日歐洲帝國主義的統治息息相關,同時也包括了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原住民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除了電子遊戲之外,遊戲和殖民主義的連結早就已經不是新奇的事物,在電子遊戲出現和流行之前,二者之間的互相反映就已成為被殖民者表達不滿和反抗殖民主義制度的方式。在2001年的寶萊塢大片《印度往事》(Lagaan)中,現實中的體育運動——闆球,成為讨論遊戲與殖民主義的媒介,該片獲得奧斯卡提名後更是産生了全球影響。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遭遇旱災的印度村莊,作為征服者和殖民者的英國人向村民征收不切實際的高額土地稅。英軍指揮官拉塞爾上尉給了村民們一個選擇:如果對闆球一無所知的村民們能夠在闆球比賽中擊敗英國人,就不用繳稅,否則他們即使砸鍋賣鐵也必須把稅交齊。電影講述了主人公布萬如何設法訓練“村隊”,并在英國人的遊戲和英國人制定的規則中打敗英國人,此外還講到主人公克服印度傳統的種姓偏見而建立起一個印度“全民球隊”。
電影《印度往事》海報。
在這部電影中,闆球這項運動遊戲所代表的不僅是被殖民者對于殖民者所施加的暴政的反抗,而且涉及到擺脫殖民的手段和殖民結束之後的社會難題——通過非暴力方式獲得和解與獨立,并在獨立之後的印度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平等社會。來自于英國的闆球遊戲預示着西方文明所施加給印度規則與“文明”,而印度人通過掌握這一外來文化反過來融入殖民者的社會并且打敗殖民者,也憑借着外來文明的刺激而改造和消除了本土文化中的“糟粕”。
同樣,電子遊戲中也常有類似的主題和立意。然而作者同時也意識到,以反殖民為主題甚至與遊戲中殖民者為敵的遊戲,表面上是對殖民主義的反對,實際内在卻依舊存在着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就像在《印度往事》中,闆球比賽雖然寓意着印度人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和走入現代文明的縮影,但遊戲——乃至“現代文明”本身,乃是殖民者帶來并強加給印度人的,電影本身在展現印度人的智慧和勇氣的同時,也承認了殖民制度給印度社會帶來的“改造”和“進步”。英國的闆球遊戲本身蘊含着奮鬥、團結和平等的内涵,這些西方人帶來的現代精神幫助印度人戰勝了傳統文化中的懶惰、自私和等級制度,是以看到這部電影的英國人也可以自诩是為印度社會帶來了文明的“解放”。
《刺客信條3》遊戲海報。
類似地,《刺客信條3》也是一部批判帝國主義的遊戲,盡管這款遊戲精心地提供了最好的情節和畫面效果,但是電子遊戲中的土著英雄,以及遊戲中所建構的其他曆史元素都表明,遊戲的視角是建立在西方人的主流價值觀之上,西方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其他種種英雄行為的核心被植入了一個具有土著居民外貌特征的男子身上,是以這款遊戲的最終使用者依舊是白人、男性和西方人。(Shaw 2015, 15)
代表西方對華人刻闆印象的“傅滿洲”。
一個由想象所建構的具有鮮明異域特色的他者圖像,最終還是用來滿足傳統上殖民者社會内的價值觀和追求,這本身預示着遊戲玩家認同殖民者對于殖民地的“改造”,并欣賞被殖民者在精神氣質上的馴服。然而,當涉及到身份問題時,在殖民主體中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沖突心理。一方面,西方人對殖民地的刻闆印象加深了其自身對于其他民族的陌生感,并不經反思地将陌生群體和固定詞語聯系在一起:愛爾蘭人往往愚蠢,中國人總是高深莫測,而阿拉伯人則是暴力分子(McLeod 2010, 53)。另一方面,當殖民者基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來解釋他們在殖民地所見到的現象時,他們相信自己所歸屬的“先進文明”可以無所不包地解釋殖民地的“落後”與“愚昧”,并且自以為是地忽視了異民族的文化背景,相信在“改造”之後原住民将秉持和自己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追求。
那麼,電子遊戲又是如何将這些激烈的沖突沖突與宏大的殖民地景象展現給遊戲玩家的呢?作者認為,這是一個迄今為止很少受到關注的話題,它涉及到電子遊戲與殖民主義的關系以及帝國是如何“重制”的。将帝國主義的空間性問題與電子遊戲的空間聯系起來,才能更直接地探讨帝國主義。
《帝國》遊戲畫面。
作者認為《帝國》遊戲的地圖中就明确了後殖民空間的混合屬性。這些地圖既是殖民者劃出新領地的地圖,也是玩家開始将世界曆史轉化為個人故事的空間,進而創造自己的殖民故事。(Lammes 2010)個人曆史與殖民主義邏輯交織在一起,并由殖民主義邏輯建構出來,這便是遊戲設計的内在假設。《帝國:全面戰争》讓玩家占領23個地區——包括印度、佛羅裡達、直布羅陀、冰島、新法蘭西等地區,其邏輯始終與它對空間性的認知有關。而在遊戲《無人的天空》中,玩家要在無窮的星系中探索和生存,它允許玩家命名行星和地點,甚至新發現的種族和物種,這一切再現了一個殖民探險家的夢想——就像命名珠穆朗瑪峰一樣,命名行為對于帝國的擴張主義和探險家(殖民者)的個人理想具有重要且貫通一緻的意義,這也是遊戲的基本殖民假設。
穆克吉敏銳地指出,殖民擴張意味着地理環境與樣貌的變化,這甚至超越了地圖上的線條和名稱。一旦一個地區被占領,地圖就會重新繪制,并帶有鮮明的殖民者色彩。在《弗洛拉的帝國》(Herbert 2011)一書中,作者尤金尼亞·赫伯特(Eugenia Herbert)描述了在印度的英國殖民者如何努力用他們的私人花園和進口植物來改變當地的景觀。而外交、貿易、戰争、交換技術和資金,是定義地理變化的其他關鍵因素。
《文明5》遊戲畫面。
外交、貿易、戰争、交換技術和資金往往是殖民主題遊戲的重要情節。這些内容本身展現着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和工業化,是以,盡管隐含着對土地、資源、财富甚至奴隸的貪婪占有,殖民主義卻被描繪成一種以純粹的金錢交易為标準、可以通過掌握财富來赢得勝利的良性競争遊戲。這樣一種渴求資源的地緣政治設定,也造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二進制對立。這種二進制主義的目的是攫取較弱國家的财産,并将其納入帝國的經濟體系,確定其他與之競争的帝國列強處于相較自己的不利地位。(Walberg 2011, 24)在《文明5》等遊戲中也有類似的設定:殖民者熱衷于在殖民地建立起資本主義和嚴格的等級體系,而周邊設施,如港口和倉庫的建設,是為了引導玩家在宗主國和殖民地建立集權控制和等級制。
為了更加生動、全面地展現宗主國-殖民地體系的狀态與互動,遊戲開發者還在《帝國》加入了一個關鍵元素:抗議。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會憤怒、會請願、直至發起暴動。是以,這些遊戲帝國的空間超越了傳統的空間概念,而進入到生活空間的角度。當玩家在另一款遊戲——《星際穿越》中建構自己的帝國藍圖時,除了領土地圖外也一樣還有許多供玩家想象的生活空間,如勞工騷亂、外交糾紛和建築營造。
對于殖民地的居民和原住民,要了解他們在後殖民主義的身份問題,就不得不讨論奴隸制和歧視的問題。《生化奇兵:無限》涉及到奴隸制問題。電子遊戲設計師亞曆杭德羅·全-馬德裡(Alejandro Quan-Madrid)描述了他在遊戲中的經曆:他有機會射擊一名被綁住的黑人女子和一名白人男子,他猜測他們是一對情侶,白人男子請求人們寬恕該女子。(Quan-Madrid 2012)穆克吉認為,殖民時期對種族通婚的恐懼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緻,黑人婦女沒有話語權的事實也顯而易見。遊戲中的一個角色思考着男人和奴隸的差別:男人可以選擇,而奴隸隻有服從。遊戲認識到“奴隸”在殖民體系下的意義——奴隸不屬于人類。此外,在遊戲機制中,解放奴隸本身也成為了一個動機不純的行為——遊戲會根據被釋放奴隸的數量來獎勵玩家——自由的奴隸成為遊戲的貨币,這與遊戲一開始的崇高意圖完全相反。
《生化奇兵:無限》遊戲海報。
在後殖民主義史學中,殖民地的過去常常被視為是殖民勢力根除和重寫本土曆史的過程。許多電子遊戲嘗試着從批判和“他者”的角度去呈現曆史。一方面,雖然電子遊戲聲稱能夠提供對曆史的批判性解讀,但它們往往最終會回歸和支援主流叙事,另一方面,随着遊戲的發展,它們會不斷地通過架空曆史和個體解讀來挑戰主流叙述。
電子遊戲作為一種多元媒體,其允許玩家創造他們自己的故事,是以,基于曆史情境的政策遊戲得以有效地從反事實的角度演繹曆史事件。玩家可以用不同方式重新體驗情境,也能夠從自己的遊戲經驗中不斷學習。在後殖民曆史方面,電子遊戲涉及規範曆史話語的邊緣叙事,包含了反曆史事實的假設場景,也創造機會去代表那些淹沒在曆史中的渺小人物來發言。作為後殖民曆史學家,對過去的探索包括以不同的方式書寫或重制那段曆史,而電子遊戲作為一種書寫和體驗後殖民曆史的媒介也是如此。
作為後殖民史學家,作者也意識到遊戲的時間性在了解帝國主義上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而且特别強調遊戲所代表的曆史背景與遊戲本身的重疊與颠倒。曆史有可能重演,昔日被殖民的國家現在變成了開拓領土的殖民者,這種角色的颠倒仍然符合帝國主義的邏輯——這不是後殖民主義,而是新殖民主義。(Mukherjee 2017, 96)通過演繹那些原本隐藏在主流曆史叙述中的另類可能性(如假設歐美的帝國主義通過與曆史事實不同的方式剝削壓榨殖民地,或者設想亞非來國家反過來殖民歐美發達國家),我們有可能得以探索後殖民時期,史學所關注的曆史多元性,進而重新審視我們今天乃至未來所要面對的殖民主義的新形式。如果電子遊戲能夠從後殖民的角度呈現曆史,那麼它們所叙述和展現的便是關于帝國的話語。
《帝國時代》遊戲畫面。
不管玩家是來自以前被殖民的國家還是其他地方,在涉及殖民主義問題的遊戲中,電子遊戲媒介同時提供了奴役、抗争、精英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可能性——這是玩家對後殖民時代的了解和體驗。(Mukherjee 2017, 19)然而我們也會意識到,遊戲規則往往傾向于會促進殖民主義,就像在《帝國時代》和《文明》等系列遊戲中所反映的那樣,遊戲中的更新和勝利是通過增加對殖民地和原住民的控制與剝削來實作的。
盡管存在這些問題,電子遊戲依然在呈現後殖民主義話語的多樣性和可能性方面表現出了相當大的潛力。電子遊戲從多個角度再現殖民地的生态,這能夠幫助我們獲得無法通過其他傳統方式來獲得的體驗。即使玩家将自己的角色等同于“殖民者”,這種認同也使人們更加身臨其境地從殖民主體的位置思考身份問題。此外,演繹另類曆史的可能性同時為延續或批判帝國的邏輯提供了機會。
電子遊戲已經經曆了一段漫長的曆程,從刻闆地美化殖民主義到嘗試呈現殖民主義的排他性與壓迫性。在遊戲開發中加入後殖民主題的同時,遊戲研究也開始關注與後殖民主義相關的關鍵問題。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研究正在迅速發展,而後殖民主義作為一個互相關聯的主題,正處于遊戲研究的最前沿。
完成了後殖民主義的主題到電子遊戲研究的延伸後,作者亦雄心勃勃地想要将這一話題推廣至更加廣大的範圍——置于網絡文化的視野内。盡管今日的網絡文化看似在不斷地消解和同質化網際網路使用者的身份差異,使得所有網民不分地域、種族、貧富,隻要有一台接入網際網路的裝置,就都能夠在網絡上享有“相同”的話語權,不管螢幕背後的個體如何,他們在網上沖浪中都是一個個沒有差别的平等個體,但這種看似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願景,實際上隻是一種對于“無種族、無歧視”的幻想。
在資訊時代,網絡文化研究未必能夠消除存在已久的種族主義本質,而在資訊、财富和技術不平等的社會裡,歐美發達國家的網站和占有社會資源的精英群體始終控制着資本和勞動力,它們操縱和決定了所謂的“熱點”、“真相”、“身份”。網絡文化的問題已經在後殖民時代進一步顯現出來,殖民的實質并未從我們的世界裡消逝。當特斯拉電動車以更好地為使用者服務的名義而事無巨細地收集各種社群資料乃至隐私資訊,今天的殖民不再是對于領土和其他實體實體的掠奪與壓榨,而是在人們不知情甚至主動同意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對于隐私權或者數字資訊的攫取,這種“新殖民”的後果将可能給殖民者更大的利益和權力,以及對于被殖民者在财産、資源乃至生命上的更嚴重威脅。
最後,縱觀全書中,作者讨論了關于殖民地的刻闆印象的問題,以及電子遊戲中關于殖民和後殖民主題的空間、身份和多元性建構。後殖民主義的話語有助于我們了解西方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霸權主導地位是如何建立的,并在此基礎上從多元化的視角中撼動這種既有的結構。遊戲正是傳達這種多樣性的強大媒介——闆球遊戲颠覆了殖民地的秩序,而關于遊戲帝國建設的政策遊戲則可以修改現實中的殖民制度,進而對殖民者的規範體系與優越論提出挑戰。遊戲本身成為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話語的一種重制。作者還試圖彙集各種立場,他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鼓勵該領域進行進一步的建設性讨論。
參考文獻:
[1] Loomba, Ania. 2005.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 Shaw, Adrienne. 2015. Gaming at the edge: Sexuality and gender at the margins of gamer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3] McLeod, John. 2010.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2n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Distributed exclusively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4] Mukherjee, Souvik. (2017). Videogames and postcolonialis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5] Lammes, Sybille. 2010. Postcolonial Playgrounds: Games as Postcolonial Cultures. Eludamos. Journal for Computer Game Culture 4 (1): 1–6.
[6] Herbert, Eugenia W. 2011. Flora’s Empire: British Gardens in Ind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7] Walberg, Eric. 2011. Postmodern Imperialism: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Games. Atlanta, GA: Clarity Press.
[8] Quan-Madrid, Alejandro. 2012. BioShock Infinite Forces Players to Confront Racism (Hands-on Preview). VentureBeat. n.p., 12 July. Web. 23 November 2016.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