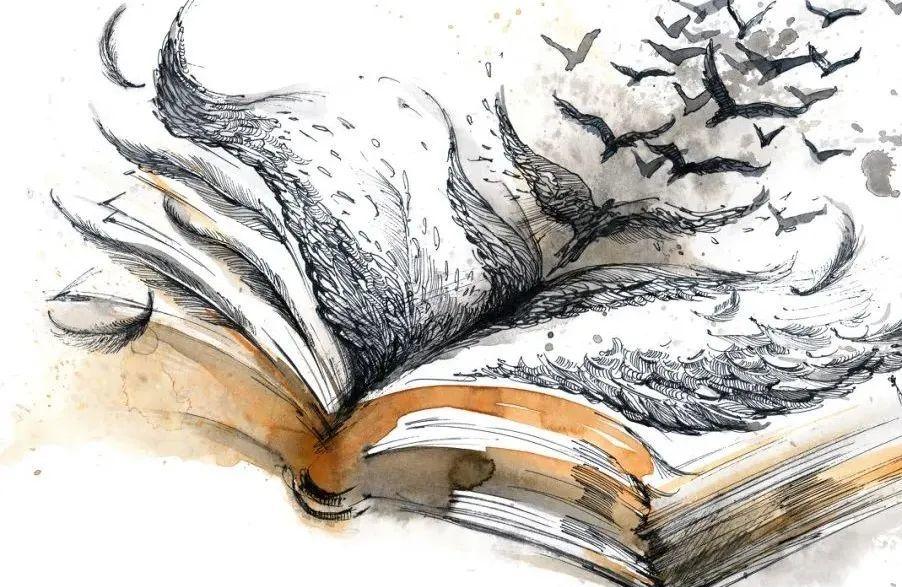
圖檔來源:圖蟲創意
“帝國主義”和“帝國”已大緻退出當代政治的舞台,但對帝國的研究卻不是一門“過時”的學問。不論是《星球大戰》還是去年熱映的《沙丘》,都展現出大衆文化對帝國想象與帝國符号長久的癡迷。更重要的是,解剖和洞察帝國的曆史并不隻關乎過去,驅動帝國興起、适應、衰敗的動力和邏輯,在今天的民族國家内也同樣存在。是以,對帝國的了解也有助于人們更好看清今日的危機,并尋找可能的解決之道。
學者鄭非打算用三本書的篇幅探明“帝國”這一政治組織的興亡之理。這一系列的頭兩部《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已經面世。鄭非在廣泛總結學界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架構,通過對具體案例的細緻拆解,質疑了一些流傳甚廣的習見。在鄭非看來,帝國從曆史舞台中落幕并不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崛起的必然。真實曆史的互動機制是複雜和充滿偶然的。面對現代性和啟蒙帶來的挑戰,帝國也努力适應并變革自身,試圖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掙得生存的權利與繁榮的機會。這些嘗試的成敗及其遺産還在塑造和影響着當今的世界。無論知識與社會怎樣進步,人類對待自己的過去都理應有更多的好奇與謙卑。
《帝國的技藝:統治不可統治之地》
鄭非/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頁folio 2021年11月
《帝國的失敗:為什麼會有美國》
|訪談|
經濟觀察報:《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是您“帝國”三部曲的前兩部。您為何對“帝國”這個概念如此着迷,并且試圖用三部曲來闡述?
鄭非:帝國這回事,在現實中已經是一個被抛棄的事物。盡管有的時候,我們仍然會用某某帝國來稱呼這個世界上勢力範圍很大、盟國很多的國家,但是彼此心知肚明,帝國在此處是當形容詞用的,用以顯示一國國威顯赫、影響深遠廣大。作為政體與國體的“帝國”,卻是不複存在了的。
為什麼帝國會從這個世界上消逝?這裡有兩種傳統說法:一種認為,“小國之堅,大國之擒”這回事在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是反過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由于内部組織嚴密,享有很高的公民認同感,相對于通常而言廣土衆民、認同多樣、組織較松散的帝國來說,要可靠、有力的多。是以,現代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是競争進化的必然結果。另外一種認為,帝國的解體主要是因為它的邊緣地區出現了地方民族主義,而這些地方民族主義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戰争”——靈活堅韌的大衛打倒了龐大臃腫的歌利亞。
這兩種觀點有共通之處,那就是都認為帝國很“弱”,是前現代和落伍的東西。它主要依賴強制、欺騙與隔離來維系自己的統治,缺乏回應性。在一個大衆日漸覺醒的時代裡,随着各族群逐漸凝結成政治實體,帝國在内遭到地方民族主義的挑戰,在外則難以同一體化的民族國家進行國際競争,是必然要崩潰的東西。簡而言之,這正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那個著名的論斷:“帝國與民族内在不相容”。
這兩種傳統說法都有一定的問題。如果第一種說法是真的,在十九世紀我們就應該看到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兩條道路的強烈競争,然後帝國解體敗下陣來。但實際發生的事情并不是這個樣子,那個時代的強國無一不以成為帝國為榮。十九世紀晚期法國總理茹費裡是這麼說的:“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一個民族是否偉大在于它遵循怎樣的發展路徑……如果隻是向外傳播文化,卻沒有實際行動,不參與世界事務,永遠站在歐洲,而将對非洲和遠東的擴張視作陷阱和危險的舉動,如果我們還試圖建立一個偉大的國家,我保證這樣的态度會使我們的國家很快走向終結。因為我們不再是一個一流的強國,而會淪為三流甚至四流國家……法國不隻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必須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換句話說,在茹費裡看來,現代民族國家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就是“偉大的國家”,即帝國。反過來說,一個現代民族是否能擁有一個帝國,就成為了這個民族的試金石。在當時,參與列強競争的無一不是帝國——既有英法這樣的海洋帝國,也有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這種傳統的大陸型帝國。十九世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帝國與民族建設實際上是一體的。
至于第二種說法,有點後事者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味道。過去我們常常把帝國中心-邊緣緊張關系産生的原因說成是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但在很多場景中,與其說地方民族主義是緊張關系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緊張關系的結果。坦率的說,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發明的産物。比起文化、血緣來說,政治沖突在促進人們的民族認同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起帝國中央來說,邊緣地方差不多總是比較弱小群組織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勢力強有力的支援,或者是帝國被極大削弱、面臨崩潰之際,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開始就尋求自治和獨立,而是希望進行改革、獲得尊重、分享權力,不管這是出于利弊分析、強弱對比,還是傳統與習慣如此。一般來說,是事态的發展逐漸使他們激進化的,是政治沖突本身逐漸劃清了社會界限,進而“民族化”了這些地方社群。民族主義往往是帝國内部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帝國沖突的原因。
從學問的角度來說,鄙著《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就是在尋求“帝國消逝”的第三種解釋。
經濟觀察報:我們現代世界的政治理念和實踐是否完全排除了帝國作為一種政治組織形式的合法性?如果說這是一個事實,那麼從您的比較研究來看,這是現代曆史邏輯的某種必然,還是混合了許多曆史的偶然?
鄭非:我不知道帝國是不是被“完全排除了”。
在理論上,現代世界确實是要求一個較勻質化的政治社會,也要求一個對本地人群負責的政府,但這是不是意味着由許多不同的人和地方組織起來的國家天然的就要分裂開呢?你會發現,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其實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是不夠自洽的。他們通常都反對帝國,認為帝國是一個民族對另外一些民族的壓迫。但如果你問他們現代國家裡那些少數族群、邊遠地方是不是都應該獨立出來自建國家,他們大多也會持否定态度。大多數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在現代,某個族群要求進行自決的需求應該首先在現有國家的架構下運作。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塞缪爾·亨廷頓在若幹年前,曾經很尖刻的評論道——“20世紀對政治離婚(也就是分離主義)的偏見,和19世紀反對夫妻離婚的偏見一樣強烈。”當有着深深敵意的族群團體“不能繼續生活在一起”時,他補充道,“他們也隻能繼續生活在一起。他們别無選擇。”
何厚此而薄彼呢?
在曆史上,我們确實可以找出許多帝國遭到邊緣地方挑戰的例子,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找出相當多相反的例子,可以表現出邊緣地方并不反帝國。
比如,一直到1776年獨立宣言釋出之前,北美大陸會議的口号都是“恢複我們作為英國人的自由”。從當時人們的言論上來看,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迹象,倒是相反,許多日後的革命者,比如弗蘭西斯·霍普金斯和約翰·亞當斯等人,還口口聲聲宣告自己的愛國之心與英國認同。
又比如,在法帝國去殖民化過程中,其實有相當多的非洲殖民地上司人并不心甘情願。學者觀察到,西非地方的民族主義在1950年之前隻有微弱的存在。實際上,當時普遍存在的是“大法蘭西的思想和法國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理想”。塞内加爾首任總統列奧波爾德·桑戈爾在1955年說道:“我所擔心的,就是……我們可能脫離法國。我們必須留在法國,不僅留在法蘭西聯邦,而且留在法蘭西共和國。”科特迪瓦首任總統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在1951年說道:“讓我們在這嶄新的一頁寫下一個誓言:将非洲變成法蘭西聯邦中最美好、最忠誠的領地。”這些非洲上司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哪裡呢?在戴高樂執掌法國政權後不久,戴高樂讓法屬殖民地舉行公投,決定是加入法蘭西共同體還是選擇獨立。除了幾内亞外,所有國家都選擇了共同體。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同樣看不到各民族争先恐後脫離帝國羁絆的情況。
再比如說,過去有人将哈布斯堡帝國稱為“各民族的監獄”,但是,捷克人帕拉斯基在1848年緻信給德意志聯邦法蘭克福議會,卻說道:“(奧地利帝國)的存在、完整和鞏固極其重要,這不僅僅對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對于整個歐洲、人類和文明來說都是如此。”“如果奧地利國家這麼多年并不存在,我們就必須為了歐洲甚至人類的利益而努力盡可能快地創造它”。20年後在另一處,他又說道,“我們在其他地方不會比在奧地利更好的儲存我們的曆史-政治實體,我們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沒有願望,也沒有政治企圖來超越奧地利。”到了一戰,帕拉斯基的這個意願似乎還是很頑固地保留在了捷克社會中。簡·伯班克和弗雷德裡克·庫珀觀察到,“1914年奧匈帝國内部不同的‘民族’并沒有把戰争當作分裂自己的機會”。
如果我們不看後果,而是回到曆史進行時中,在很多時候、很多地方,我們其實是找不出什麼帝國衆叛親離、非要崩潰的迹象的。
為什麼帝國不能像一個普通的多民族國家那樣就這麼維持下去?
我承認随着民主與民族時代的到來,國家面臨着某種“收縮化”的壓力。帝國,是一個廣土衆民的事業,就自然而然的更加能感到這種“收縮化”的壓力——組成帝國的多元成分之間如果要繼續共存下去,如果帝國還想順利地管理各人群,上下、左右之間就必須建立某種“社會契約”,約定“名份”。而這些“社會契約”卻是很難達成的。美國占領菲律賓時的總統是麥金萊,他曾經有過一番這樣的言語——“我夜複一夜地走在白宮的地闆上,直到午夜,先生們,我毫不羞愧地告訴你們,我跪下來,不止一個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禱,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難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獲得一塊新領土之後會有麥金萊這樣的苦惱。
那這種難是不是徹底讓帝國無法再作為一種有效統治方式存在呢?卻也不一定。因為帝國的消逝,從曆史上看,主要不是因為帝國在内部遭到了什麼嚴重的挑戰,而是帝國之間的戰争瓦解了他們——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帝國互相摧毀的戰争,戰後世界的主要意識形态是列甯主義和威爾遜主義,而這兩個主義都對帝國和帝國主義持相當批評意見,蘇聯和美國兩個大國的超強實力,都使得二十世紀成為帝國的大退潮期。
換句話說,諸近代帝國的崩潰,從曆史上看,主要是外部強加的,而不是由于自己治理不下去了。
對您的問題,我最後的答案恐怕是:不,我不知道帝國的消亡是偶然還是必然。理論與曆史實踐之間沒有對上号,讓我無從作答。
經濟觀察報:不管是傳統的領土帝國,還是19世紀的殖民帝國,都在20世紀面臨轉型問題。從結果上來看,擁抱了“自由帝國主義”的殖民勢力最終都無法承擔帝國内部的張力而最終解體。就像是最近出版的書《王公之淚》裡描述的英印帝國那樣,您是否認為“自由帝國主義”不可避免的淪為僞善和自我沖突?而明确厭棄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解決方案的傳統帝國是否也表現出意料之外的韌性?
鄭非:根據我的了解,所謂“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主要指的是十九世紀中晚期的一種政治思潮,當時有些人認為帝國的統治對原住民社會是有益的,是以是歐洲文明國家的使命和責任。他們認為較先進的歐洲文明國家應該将自己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模式輸入到較落後的世界中去,這樣帝國對于彼此都有好處。無論是約翰·密爾還是托克維爾,都是自由帝國主義的信奉者與鼓吹者。
自由帝國主義有講得通的地方。譬如馬克思雖然痛斥殖民主義的罪惡與野蠻,但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也認為不列颠在印度的征服有着正面的一面。恩格斯也指出,“(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對于文明的進展卻是有意義的……擁有文明、工業、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對開明的現代資産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處于野蠻社會狀态的擄掠成性的強盜比起來,畢竟略勝一籌”。作為意識形态上的對手,他們總不會故意說好話吧。
問題在于,自由帝國主義确實像您所說的這樣,最後不免于僞善與自我沖突(雖然起初未必如此)。
我們拿英國和法國來舉例好了。
先說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梅特卡夫在《新編劍橋印度史》一書中有一個觀察:“英國人所慮及的印度,在相似和差異這兩種理念之間存在着一種持續的張力……英國人對印度的看法從來沒有呈現為一個單一而連貫的思路。有時,英國人将印度人視為像自己一樣的人……另一些時候,他們又強調他們所确信的印度差異的持久特質。甚至有時候,他們同時讓兩種看法共存于他們的思考之中。”
這種糾結并不是無因由的。簡單來說,對印度人到底和英國人相似/差異到何種程度的認知,實際上關切着印度究竟在帝國内有何未來。如果認為兩者相似,那麼英國就負有文明教化之責,印度将預期逐漸實作社會進步,同英國實施同樣的法律與政治制度,獲得“英國性”。如果認為兩者有本質差異,那麼就隻能“漢法治漢,番法治番”,印度就隻是一塊異域。
梅特卡夫的結論是,在整個英統時期,最強有力影響着英國對印度認知的,仍然是差異思想。在征服早期,英國的行政部門強調過對傳統的印度習俗、法律和宗教加以尊重和容忍,也強調跟傳統社會精英合作,利用既有的政治結構進行統治。這既是對政治與社會現實的尊重,同時也是“印度隻配專制主義統治”認知的結果。到了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随着自由主義思想在英國逐漸占據上風,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也決定在印度實施改革,開始着手把印度人變成英國人。比如輝格黨曆史學家、政治家麥考萊在1835年呼籲對印度文化和社會進行徹底改造,以造就“在品味、觀念、道德及思想方面的英國人”。這個就是自由帝國主義的言語咯。但是1857年印度大起義将這一想法一掃而空,在印度的某英國官員在回顧起義緣由時寫道:“意圖将歐洲政策強加于亞洲群眾身上的這種緻命錯誤……将來必須要加以糾正。”另一位在1859年執掌印度事務部的英國官員也說道:“在最慈善的情感的感召下,按照我們的正義與公正的觀念,我們陷入的誤區是,引入了一個對于群眾的習俗和願望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體制。”他的結論是:“我們應該盡量采用和改進該國現存制度體系中那些可用的及對我們自己有利的東西。”換句話說,英國人覺得是過激的改革引發了叛亂,滿懷的是“狗咬呂洞賓”式的委屈,他們決定一切複原。
是以英國人的自由帝國主義不免于僞善。
法國人在法帝國的統治從表面上看,其實要比英國更“自由帝國主義”。比方說在1881年5月5日,法國著名的共和主義政治家甘必達在紀念廢除奴隸制(1794年)的宴會上發表演講,提議為“海外法國”幹杯,并說道:“人權宣言沒有根據膚色或等級來區分人……正是這給了它以莊嚴與權威……它并沒有說‘法國人和公民的權利’,而是說‘人和公民的權利’。”法國殖民史的研究者史蒂芬·羅伯茨對此的評價是,“自由、平等和博愛彌漫在空氣中,這都建立在拿破侖法典和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正統觀念上。法國隻把帕比提、達喀爾和因蘇拉看成是巴黎的遠郊。”
澳洲曆史學家羅伯特·阿爾德裡奇也指出:“貫穿整個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殖民政策的概念是‘同化’……這項政策的目的是,……在時機成熟時,将非洲人、亞洲人和島民變成不同膚色的法國男人和女人。”
法國人不僅這麼想,而且還真的部分這麼做了。但是法國人到最後,實際上也無法接受同化政策的後果。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有越來越多的法國人覺得帝國是累贅而不是資産,每年從本土吸走大批援助資金而沒有回饋,讓外人成為法國公民沖擊法國社會的穩定,而法屬非洲上司人所希望的那種既個人平等又多元文化式的聯邦政體與法國既有政治實踐的沖突越來越大。弗裡德裡克·庫珀在讨論這段曆史時的結論是,“法國人和非洲人一再被夾在他們想要的政治和他們能得到的政治之間”。這種不協調可以說是法帝國破産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說,法國人倒是不那麼僞善,但是“自我沖突”卻是它帝國政策的必然結果。
那不搞自由帝國主義的傳統帝國是不是更有韌性呢?從曆史上說,肯定不是。比方說俄羅斯帝國。我們很難說俄羅斯帝國在推行什麼自由主義日程。比如在帝國末期,它在芬蘭相當程度上收緊了控制,破壞本地原有的憲法和自治。
芬蘭人原本對俄羅斯帝國是很有好感和向心力的,這是因為俄羅斯人吞并芬蘭的時候,給予了芬蘭人相當大的自治權力。但是随着俄羅斯帝國的打壓,越來越多的騷動就出現了,這首先展現在越來越多的芬蘭人移民到其他國家去了。接着這展現在恐怖主義舉動中。比方說1904年6月9日,一位年輕的政府雇員尤金·紹曼(他的父親是俄羅斯軍隊的前将軍,也是參議員)在參議員大樓裡面刺殺了沙皇的芬蘭總督博布裡科夫後,舉槍自殺,給沙皇留下遺書,說道“這種方法很暴力,但這是唯一的方法。我知道陛下心地善良,意圖高尚,是以我懇求陛下去了解一下帝國的真實情況。”
1912年4月,一位芬蘭貴族在一封信中表達了他的同胞們普遍持有的一種心态:“除了改變目前所有權力關系的重大歐洲或世界事件,沒有什麼能拯救我們。”這句話其實是在說,一旦有事,那麼芬蘭人就會行動起來。芬蘭史的研究專家倫納德·倫丁歎道:“無論俄羅斯化的某些理由一開始看起來多麼合理,芬蘭的事态發展已經證明這種計算是根本錯誤的。一個絕大多數人忠誠的民族被疏遠了,芬蘭民族意識被強化了,一個敵人被不必要地創造出來了。”
實際上,不止是芬蘭,俄羅斯帝國在其帝國末期,制造了無數“不必要的敵人”。說老實話,我看不出來這樣的帝國有什麼韌性可言。
經濟觀察報:正式的帝國可能已經走入曆史的背景,但是帝國的邏輯和動力可能還在當今的政治演化中非正式的存在。對于帝國的研究對澄清和了解當代政治,您能不能提供一些見解?
鄭非:帝國在政治上的作用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有些帝國的存在,确實遏制了一些區域中的地緣、族群沖突,但另一方面,一戰之後對帝國的批評也是有道理的——帝國是對世界的一個分割,它破壞世界經濟的自由流動,它們之間的競争又帶來了極大的戰争風險。但是如果我們将眼光從國際關系領域縮回到帝國的内部統治手段這件事上,那麼帝國還是對我們可以有所教益的。
帝國的曆史經驗中有一樣,我覺得特别值得注意和學習,那就是凡普世帝國通常都能接受主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對其由多民族屬民構成的屬地,通常它們都不強求“皇權下縣”和一緻管理。在很多時候,帝國的統治手法是講究“難得糊塗”四個字的。埃德蒙·柏克在總結英帝國統治教訓的時候,就說道,一國對其屬地的主權,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必定無限,但是從實在上講,是根據各地環境、曆史之不同而有權利邊界的,為政者需要自我克制,尊重這一自然形成的邊界。
帝國的曆史經驗中,我認為值得重視的第二項就是成功的帝國通常都能夠意識到中心—邊緣劃分的存在,不以國家一統為當然,意識到中心—邊緣應該是某種合作關系,意識到邊緣區在心理和政治上都可能需要更多的特殊保護,意味到核心區和邊緣區的政治、社會精英在政治等級之外應該建立某種常态的交流管道,進行政治磋商和人際交往、人事吸納。
從這兩項經驗出發,我認為,在異質性較強、規模又大的現代民族國家裡,政治精英們也許應該多看看帝國史,以便在這些手法上向那些成功的帝國有所學習。
閱讀作者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