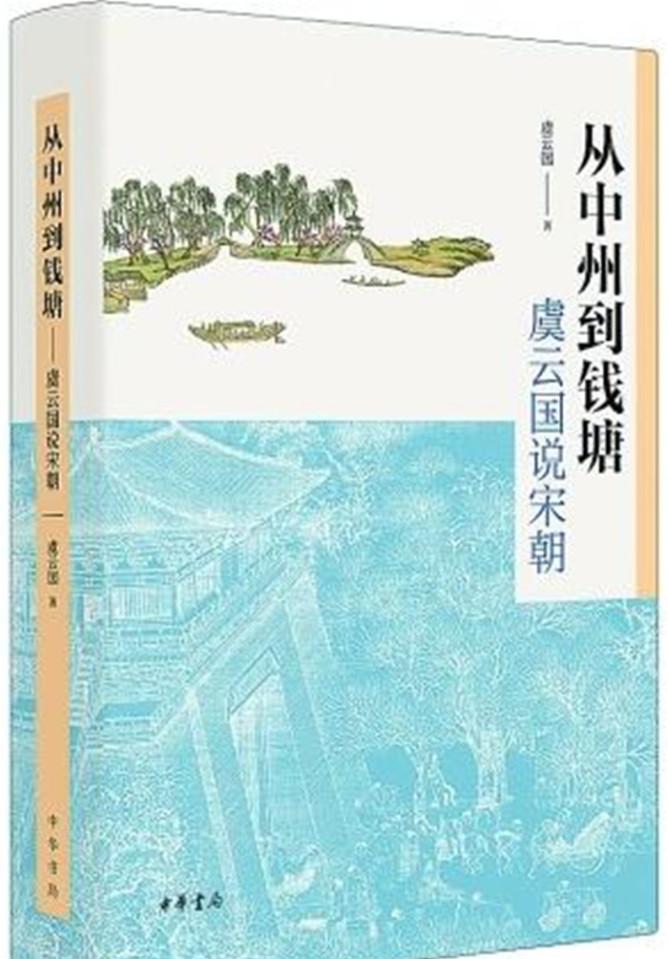
《從中州到錢塘》
虞雲國 著
中華書局出版
讀罷虞雲國先生的新書《從中州到錢塘》,一個很深的感受是作者知人論事時的冷靜與克制。特别是置于當下這個對宋朝評價持兩極分化的時代——貶者陷于“積貧積弱”的弱宋傳統論述而不能自拔,贊者将宋朝視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朝代——更顯得這本書的公允與理性。
在《從中州到錢塘》中,作者寫到了不少宋朝皇帝,不妨一一看看作者是如何評價趙官家們的。
本書第一個重點寫到的宋朝皇帝是宋真宗,他在曆史上的關鍵詞是“澶淵之盟”和“天書祥瑞”。
在我們傳統的曆史認知中,“澶淵之盟”是一個帶有恥辱性質的不平等條約,虞先生雖然對宋真宗總體評價并不高,但還是在《再說宋真宗及其時代》中公允地寫道:“澶淵之盟是一個平等的條約(紹興和議不宜與其混為一談),也奠定了百餘年的和平格局,無疑應該肯定。”
至于天書祥瑞,本書有專文《天書鬧劇中的抗争與喑默》,将這場鬧劇定性為“純粹是皇帝自樹權威的自娛自樂,卻勞民傷财地前後持續十餘年,是兩宋史上近乎瘋魔的宗教狂熱與政治笑話”。
從總體上說,作者既承認宋真宗有容人之量,對妄議聖上者“容之而不斥”,也将宋真宗時代定義為“仍處于王朝上升期”,“士大夫政治正處于育成之中”。
曆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宋真宗本人至死都沒有弄清楚自己的曆史定位。他因為對澶淵之盟耿耿于懷,是以對天書封禅寄予厚望,視作挽回澶淵之盟之恥、全面提升個人曆史地位的“盛事”,沒想到,這反倒成為了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他可能到死也沒搞明白,他是因何榮耀,又是因何蒙羞。
如何去描述和定義一個總體評價偏中性的皇帝,虞雲國寫宋真宗提供了一個很不錯的範本。從作者對宋真宗一生兩件大事的一褒一貶可以看出,他的曆史人物觀是“溫情與敬意”和“冷靜客觀”兼而有之,不說過頭話,就事論事,将道德視角限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内,并不迷戀于建構一個過分追求同一性的整體論述。
宋朝公認最好的皇帝是宋仁宗,而評價一個好皇帝的難點在于,很容易陷入求全責備或頂禮膜拜的兩難陷阱。在《宋仁宗的仁恕與雅量》一文中,作者在一開始就開宗明義:“中國皇帝中,平心而論,他既不是奮發有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聲譽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優點就是寬容仁厚,能容忍各種激烈的批評,哪怕是對他私生活妄加非議。”“我們沒有必要頂禮膜拜宋仁宗那樣的‘仁君’……但倘若把宋仁宗與明清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專制者做比較時,孰優孰劣的公道結論還是不言而喻的”,這或許可以算是本書評點宋仁宗的點睛之筆,好皇帝既是一個客觀标準,也是一個縱向比較的相對概念,好不好,是需要比的。
這也正如作者整體評價宋朝時所說:“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長足的進步,但其所有進步都是相對的,而且是在專制政體下展開運作的;皇帝仍是國家最高決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頂層設計無不服務于君主專制集權。”
我想,這樣一種看曆史的開放和相容心态,正是我們閱讀曆史的必要性之一,也是我們可以從這本書的知人論事中可以學到的。除了一些具體的曆史結論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我養成這樣開放性多元性的曆史觀,對曆史人物多一些設身處地的了解之同情。
虞先生自然也有評價不高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就宋徽宗,傳統論述偏重于強調他的無心政事和醉心享受,以至破國亡家,但虞先生則更注重論述宋徽宗作為專制帝王的一面,凸顯他惡化北宋政治生态的一面。他在本書的《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宋朝》一文中指出:“宋徽宗繼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變法徹底變質;同時全面放逐異見派官僚,以期與蔡京等代理人獨掌中央控制權。”
而對于宋高宗這樣一位“中興之主”,虞先生的批評甚至更為激烈,這種批評同樣是基于對政治生态的破壞。他在《宋高宗的紹興體制與南宋的轉向内在》中指出,“紹興體制”是宋高宗一手打造的專制集權體制,這一專制集權格局,籠罩在整個南宋政治曆史之上,盡管在不同時段有強弱隐顯之别,卻幾乎沒有本質的變化。“以帝王術而論,宋高宗絕對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後選擇了秦桧,并且默許他登上權相之位,就是亟須有一個言聽計進而強幹有力的權相幫他确立并打理與紹興體制有關的一幹棘手政事,成則‘聖意’獨斷,敗則宰相代罪”。
除了皇帝,這本書還對兩宋的幾大權相,特别是君相關系有很精彩的論述,比如寫到了南宋四大權相,“秦桧、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南宋權相專政,累計長達70年,令人側目,也為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秦桧之為權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紹興體制之需君權獨運而主動授權的,那麼,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擅政,都是專權之勢已成,而由在位的宋甯宗、宋理宗與宋度宗無奈讓渡的”。
對于曆史人物評價,特别是所謂奸臣的評價,我個人并不反感近年來備受争議的“道德視角”,比如一個人上千年來都被說成“奸臣”總是有原因的,古人未必有我們這個時代想象中的那麼迂腐和不知變通。“道德視角”也參與建構了曆史,甚至可以說也是曆史本身,比如,你大可以認為韓侂胄、賈似道不是奸臣,但不能否認他在曆史上的确被視作奸臣,并且,去研究去尊重古人的此種“道德感”也是有意義的。
不過,尊重“道德視角”的前提是,我們也應當接受這樣一種觀念:道德視角隻是閱讀曆史的視角之一,這個視角有多重要,見仁見智。但是,這個視角不能是唯一的視角,這就像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時,也不能完全擺脫道德視角一樣,因為,我們畢竟生活在一個由觀念構成的真實世界中。
在我看來,如何評價一個皇帝或一個朝代,基于史料出發的客觀标準自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也應當寬容個人價值觀和态度的存在。司馬遷、陳壽、司馬光這樣的大史家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偏好,所謂“太史公曰”和“臣光曰”。同樣,作為當代曆史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讀者,都有權力基于自己的思想資源、社會關懷、世界觀和個人偏好,建構自己的曆史人物評價體系。當然,這同樣也有兩個前提,一是要多讀書,盡可能多地熟悉史料,空口無憑的“自由思考”和“批判式思考”是妄人所為;二是要理性面對争議和不同意見,争議永遠不是問題,我們讀曆史的目的不是解決争議,而是了解争議,争議讓曆史更充滿魅力,讓我們對曆史人物的了解更多元更深入。
如何談論曆史人物,評點曆史人物,虞雲國先生給我們開了一個範例,正如他在本書前言中所說:貼着曆史說,揣着良知講,記着讀者寫。
作者:張明揚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
*文彙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