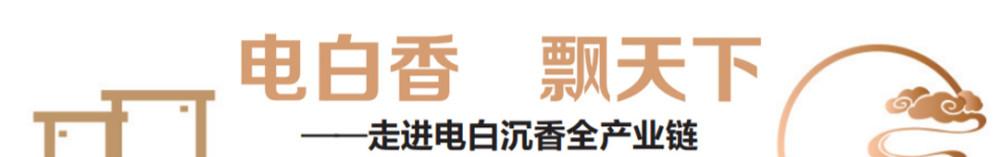
開欄語
茂名市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從生産、加工、銷售一體化發展,全産業鍊打造荔枝、龍眼、化橘紅、沉香“四棵樹”和羅非魚“一條魚”,打好産業、市場、科技、文化“四張牌”,培育一批超百億級現代農業産業叢集。
有着“中國沉香之鄉”稱号的電白,2021年沉香産業年産值已超30億元。電白沉香經營曆史可追溯至唐代,距今有1000多年曆史。
一棵沉香樹,背後有多少人艱辛探索的故事,又如何成為電白的金字招牌?即日起,《南方日報·電白視窗》推出“電白香 飄天下——走進電白沉香全産業鍊”系列報道,走進沉香培育、種植、生産、加工及銷售全産業鍊各個環節,深度透視電白沉香的曆史、現狀及未來發展。
1月5日《南方日報·電白視窗》04版特别報道。
耄耋之年的汪汝國和高善積,60多年前入深山采沉香,寫就了香農艱辛謀生的故事。
官茂有和何漢林南下采香,渡過瓊州海峽那一刻起,為電白人下海南的曆史增添了“沉香佬”這一篇章。
從采香中發現商機的汪科元、汪金利、黃春龍,依托傳統香農身份,發現了電白沉香産業的曙光。
新一代沉香人黃富藝、李鵬、劉啟豪,從其他行業轉入沉香領域,希望在祖輩已經畫出的沉香王國雛形中,尋找新的機會,補上更豐富的細節筆畫。
從深山采香,到尋香海南;從轉型收購,到商業營運;從打造産業,到尋找新機。四代人逐夢沉香深林的故事,也是電白采香人耕耘開拓的曆程。
高善積當年前往海南采香的通行證。(備注:圖中照片為其兄弟高善德)鄧建青 攝
香一代:深山尋香
新中國成立以後,電白山區一帶遍地生長着野生沉香樹(白木香),本地香農按照傳統采香法上山采香。他們在沉香木樹頭下用小鋸子将沉香結香的部分鋸下來,然後去掉白色部分,保留沉香片塊,再交收購站收購。這時期,電白沉香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
“觀珠一開始基本沒有正兒八經采香的香農,是外地人過來采香,村民知道這個東西賺錢,才跟着學的。最初采到的沉香沒地方賣,都是轉給外地香農拿到廣州去銷售。”今年82歲的高善積回憶說,以前雖然屋前屋後都能找到野生的白木香樹,但村裡人大多不懂這個。不少從高州等地過來的香農到觀珠采香,村民跟着看才學到了采香技術。同樣處于耄耋之年的采香人汪汝國,少年“識香”的經曆也有外地香農的身影。其父親那一輩,曾有廣西香農到觀珠采香,當時正是汪汝國的父親帶着他們上山尋采。
20世紀50年代,高善積初學采香,當時他才14歲;而汪汝國,也在17歲的年齡開始了香農生涯。他們将采香作為營生手段,後來走南闖北遍采沉香,又耳濡目染地影響了新一代的采香人。從這一層面上來說,他們是新中國成立後電白的第一批職業香農。
“那時候要挑着采,采最好的;最好的采完以後,才采差一點的。”對于汪汝國們來說,當時野生沉香樹數量尚盛,即使沉香樹不一定就有沉香,但随處可見的沉香樹多少讓第一代香農有些許資源富餘的惬意。
采香的通行證。鄧建青 攝
“那時候沉香沒有這麼多名稱。政府隻按等級進行收購,一等的1斤40元、二等的32元、三等的24元,還有等外品,每斤16元。”這在當時,在收入上算是挺好的副業了。
當然,收獲之中,也常伏險境。尋香常需入深林,林深則自然危險重重,除了兇禽猛獸毒蟲,甚至還有獵人的陷阱。高善積曾經兩次不慎失足,掉進獵人設的陷阱,陷阱深四五米,他硬是忍着傷痛,用手腳撐着兩側岩壁才緩緩爬了上來。
野生沉香樹繁盛供香農尋采的時間,其實也就五六年。“大概20世紀60年代,周邊野生沉香樹就很少了,要找好的樹就得走遠。”高善積回憶說,當時一部分香農仍然留在家鄉采香,少數香農則開始嘗試前往珠三角、海南一帶采香。由此,電白誕生了新中國成立以後首批外出尋采沉香的香農。
根據祖父傳下來的中國南方諸省沉香分布圖,汪汝國等十多人結夥前往海陸豐采沉香,獲利甚豐。後來,他們又從海陸豐轉到從化、增城、惠州,再折回開平、恩平、徐聞、海康(現雷州),基本上粵東粵西的山頭他們都走遍了。20世紀60年代初,汪汝國那撥采香人渡過瓊州海峽,往海南五指山采香。汪汝國稱當時的海南香農幾乎絕迹,他在霸王嶺、尖峰嶺等深山老林中見到結香經年的上好沉香,驚喜不已。
“做沉香這行太苦了,不少人都幹不下去了。”有的重新回頭種地,有的做起了藥材生意,有的當了醫生,隻有汪汝國一直沒有停下來。
除了汪汝國、高善積,當初第一批香農的代表人物還有汪慶、汪福賢、盧建南、盧建新、盧建禮、陳永福、嚴錦棠等十幾人。他們大多健在,但不少已是耄耋老人。
漫山遍野的沉香林。何偉 攝
香二代:南下海南
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香農們的故事在走南闖北中寫就。
由于本地沉香樹越來越少,香農隻能動起了“背井離鄉”的主意,赴外地采香。如當年山東人闖關東一樣,電白人很早就有下海南尋生活的傳統。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第一代外出香農的言傳身教下,電白很快又誕生了第二批外出尋采沉香的香農。這批香農人員頗多,最知名的有嚴永彬、官茂有、汪亞球、汪樹強、盧宏科等30多人。
被尊稱為“粵西沉香之父”的官茂有是觀珠大水坡村人。官茂有8歲即随父輩上山采野生沉香,20歲出頭的時候,因公社企業站把沉香經營作為搞活經濟的突破口,官茂有受命帶領一幫香農遠赴海南島,踏遍深山遍采沉香。從他率衆渡過瓊州海峽那一刻起,電白人下海南這段曆史便增添了“沉香佬”這一篇章。
往海南采香的望夫鎮南山村香農何漢林說,當年他與同伴在深山尋找沉香樹,見到一些沉香樹大到兩個人合抱都抱不過來。這般巨大的樹要幾個人兩三天才能完成砍伐采香,再加工整理成沉香發回電白觀珠交供銷社收購。
盡管發現了大量野生沉香存樹,但這一代香農卻可能是最苦命的一代。深山采香異常艱辛,他們為了尋采野生沉香,得在荒無人煙的山溝中搭起小草棚用作晚上睡覺,有時候甚至直接找個山上的岩洞,地上鋪些樹葉當床睡。每天早上不到5時,香農們就起床往深山野林裡鑽,幾乎每一步都是步履艱難。他們一天最多隻能吃上兩頓飯,一般要到晚上7時後才會收工回到睡覺的地方。白天在山上,口渴了,也不敢喝山上的泉水,若不慎喝了,很可能會得一種可怕的瘧疾。有時候天黑了找不到回來的路,他們就隻能在山上餓着肚子熬過漫漫長夜。
除了要忍受饑渴,他們還要與天氣、山螞蝗、毒蛇等作鬥争。海南多為熱帶雨林,山上一到中午常會下起大雨,香農一身汗一身雨,很容易感冒,加上山上終日霧氣缭繞,不少人患了瘧疾,最後不治身亡。一些香農不慎被山螞蝗咬到下肢,差點緻殘。如此艱難困苦的生活,幾近人類可承受的極限。多名老香農就葬身在深山老林中,再也沒有回來。
官茂有回憶說,那一年他分别帶了幾撥觀珠香農到海南采沉香,四五十人中能在艱苦環境中堅持下來的,不過七八人而已。但正是在這一批南下采香的香農引領下,電白古老而傳統的采香行業一直薪火不斷。
此外,也正是這數年間走南闖北的采香生活,讓不少香農發現了收購沉香的契機。一些采香人逐漸從其他香農手中收香及轉售,轉型成了最早一批的沉香商人;而官茂有和溫鎮先等人,也在采香和收香的過程中,發現并察覺到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沉香——奇楠,這又是電白沉香産業後來迎來巨大發展的另一道曙光。
位于電白區觀珠鎮的沉香山。
香三代:産業雛形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加速發展,香農後人也逐漸從深山野林中抽身,迎來了開辟新戰場的絕佳時期。
“我去海南采香,20天辛苦下來隻賺了100元;收購沉香,一個星期就賺了200元。”觀珠香農後人汪科元17歲也曾渡過瓊州海峽,跟随師傅官茂有遊走在海南五指山中尋采沉香。他的第一趟海南行曆時20天,賺了100元。不久,汪科元發現采香遠遠比不上收購沉香賺錢,他決定籌款前往海南收購沉香。盡管自己手上隻有80元,但成功借來3000元的汪科元還是毅然決然下了海南。一個星期後,他把3000元全部用于收購沉香,一下子賺了200元。
收購沉香的巨大商機,馬上吸引了同村不少青年。第二趟下海南收購沉香時,18歲的汪科元帶了4名學徒。三年下來,汪科元多次前往海南收購沉香,成為觀珠最早的萬元戶之一。後來,汪科元轉型為業務員,外出做起了沉香、胡椒、春砂仁等藥材生意,并順勢承包了沙琅鎮醫藥站,事業從此進入快車道。2000年前後,汪科元在觀珠、沙琅開發規模宏大的“沉香山”,人工種植白木香樹面積超過3萬畝,并開發了一系列沉香衍生産品。
觀珠人汪金利,在外出采香8年後不再跟随父親汪汝國的腳步,轉而主攻沉香銷售市場。他很長一段時間内,每年出國三四次采購沉香,足迹遍布馬來西亞、印尼、越南、高棉、寮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在當地收購沉香後即郵寄回國,這一點與當年到海南五指山采沉香,然後下山郵寄回觀珠一模一樣。汪金利後來開設了自己的沉香店鋪,又建立了沉香連鎖店,還辦起了沉香加工廠,加工雕刻沉香工藝品。
黃春龍在馬踏成立了沉香種植專業合作社。他積極引導附近群衆利用荒山種植沉香,目前其沉香苗圃每年可生産300多萬株優質沉香苗,銷往國内的廣東、福建、廣西、海南、雲南以及國外的越南、金三角等地,成為如今電白乃至粵西地區沉香種植界的翹楚。
74歲的劉基勝,并非香農出身,從年齡來說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白“香三代”。他在20世紀90年代舉全力進入沉香行業,大力發展白木香種植,于2016年前後又轉型種植奇楠苗,完整見證及參與了“香三代”的發迹曆程。如今,劉基勝所在的合作社已經在640畝的林地上種下了奇楠沉香林。以奇楠木五年可結香收成的速度,他和合作社社員正期待着即将到來的大收成。
這一代香農,幾乎完全抛開了傳統意義上的跋山涉水艱苦采香的香農形象,更多通過收購、銷售、商業運作等方式,取得了個人經濟效益的豐收,并有力推動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形成了香農的全新形象。尤其是近幾年間,與他們類似的林農在電白越來越多,他們從研發、種植、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發力,為電白沉香産業騰飛打下了牢固基礎。
沉香樹上取香。何偉 攝
香四代:尋找新機
對于祖輩而言,他們用數十年的艱辛努力,從采香、收香到發展經營,已經為沉香産業獻出了一曲絢麗的舞曲;而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眼裡,與沉香打交道,他們則希望在祖輩已經畫出的沉香王國雛形中,尋找新的機會,補上新的筆畫。
“目前觀珠成規模的電商企業比較少,尤其是在直播這一塊。我們希望用新的電商形式幫沉香行業擴大銷路。”2021年中,黃富藝和李鵬放棄已經打下基礎的服裝直播電商,從廣州回到觀珠發展沉香直播帶貨,正式投身農村電商的藍海。
“現在算初步運轉正常了,目前每月流水有兩三百萬元,希望2022年每月流水能過1000萬元。”黃富藝和李鵬創辦的漢香道直播帶貨公司目前招有36名主播,他們在直播間在沉香林中說香、售香,也在講述一個新産業的故事。
漢香道的網商之路仍在探索。1991年生的劉啟豪則已經在憧憬要創辦一個年産值30億元的沉香連鎖店品牌。“目前我們還是以家庭式、小作坊為主,産業需要整合資源,把所有散戶集中起來,把産業做大。”劉啟豪2017年停止營運土建工程公司全身心投入沉香産業,現在擔任觀珠社群黨支部書記的他希望利用觀珠現有生态優勢,在未來三到五年間發起打造一個集研發、生産、加工、銷售等于一體的高科技工業園,集聚零散資源,做大做強産業。
1984年生的高世威,經營着一家沉香工藝品公司,2015年取得全國沉香行業十大知名品牌稱号,在沉香行業已是頗有名氣的“能人”。高世威祖輩三代都從事沉香行業,但他常喜歡跳出舊有傳統,奇思妙想地生産出了沉香手機殼、沉香皮帶等産品。他希望沉香行業未來越來越有新意。
25歲的劉峰,一畢業就跟随父親劉基勝進入沉香行業。他希望用自己學習的新電商知識,幫助父親劉基勝的沉香基地進行商業模式的革新。
這群而立之年左右的第四代香農,是電白新一代沉香人的縮影,盡管他們可能從未如老一輩香農深入深山野林采香,但他們以另外一種方式,在沉香行業的“深林”中尋找着屬于自己的機會,也用自己的努力煥發着産業的新希望。
曆經四代人的耕耘開拓,電白沉香産業飛速發展。2010年,電白種植沉香面積11萬畝,一躍成為全國人工種植沉香和奇楠沉香面積最大的地區。2012年,電白沉香産業聞名中外,電白也是以被國家命名為“中國沉香之鄉”。資料顯示,目前在電白從事沉香事業的人員近4萬人,擁有市級以上沉香龍頭企業5家、區級65家,農民專業合作社1068家,家庭作坊800多家,形成了種植、加工、銷售“一條龍”的經營模式。近30億元的年産值,描繪了一個産業的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也記錄了數代人的人生。
■相關
什麼是沉香
沉香,又名白木香,自古以來被視為名貴香料和稀有中藥材,擁有獨特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的茂名市電白區,是我國天然沉香樹的中心分布區之一,有着近千年的采集、加工沉香的曆史。早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電白沉香就舉世聞名。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冼太夫人率軍征戰,将士随身攜帶的“戰地香囊”就是以沉香為主的金瘡藥。《太平廣記·草木》和《廣東通志·物産》所記載的“太宗問沉香”之典故,說的就是冼太夫人之孫馮盎向唐太宗進貢電白沉香的故事。電白沉香也被唐太宗下旨稱為“貢香”或“禦香”。到了唐玄宗時代,因楊貴妃沉迷沉香,電白沉香更是天下皆知。沉香是由沉香屬的樹種在生長過程中受傷後形成的天然混合物質,要結香就必須讓沉香樹“受傷”。樹木受蟲蛀、動物撕咬樹身或人工開鑿産生創口,樹木在受損位置凝聚樹脂,日久才成為沉香。
【采寫】南方日報見習記者鄧建青
【策劃】黃小猛劉俊
【統籌】鄧建青 劉棟銘 賴廣昭
【作者】 鄧建青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