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要達到這“平天下”的終極目标,“修身”也就成為了首要條件。
那麼,要怎樣修身呢?古往今來,對于此說法見解上也是莫衷一是。然而,在衆多不同的意見之中卻又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要求個人要做個好人,多行好事、善事。說到這裡,想必有一句詩歌已經湧入了無數人的腦中——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
這句詩也被無數人奉為圭臬,視為座右銘。但是,想必許多人并不知道這首詩的淵源,而寫下這樣一首富含哲理的千古名篇的詩人馮道甚至還被歐陽修、司馬光貶為不知廉恥的奸臣。
這首詩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故事呢?馮道又憑什麼會以“奸臣”之身份寫下一首如此富含哲理的詩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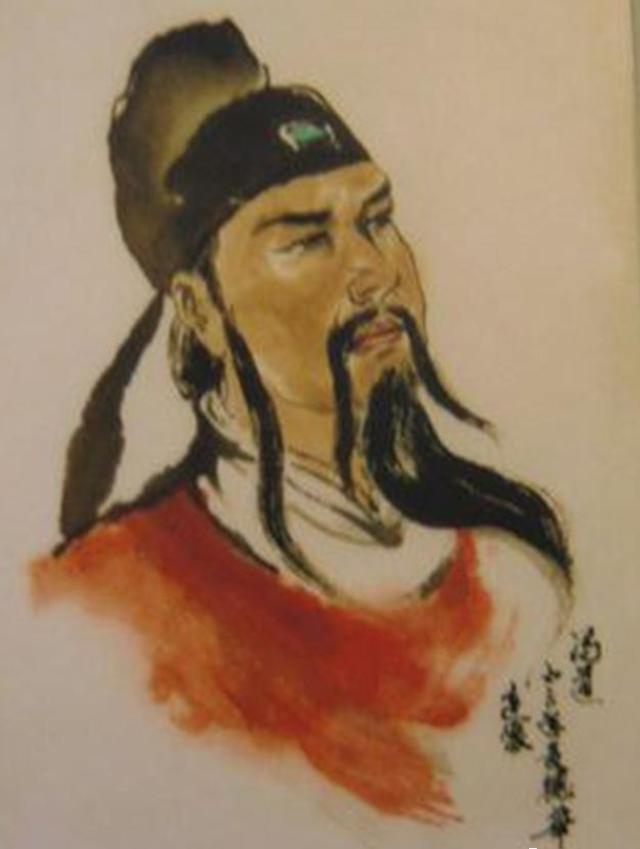
馮道其人
在歐陽修主持編纂的《新五代史》中,他對馮道的評價是:“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進而知也”;司馬光則在其編纂的《資治通鑒》中直言馮道為“奸臣之尤”——奸臣之最。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公元882年,馮道生于瀛洲景城的一個耕讀之家。良好的傳世門風,聰穎的天賦也讓馮道本可以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然而,個人的命運在時代面前卻顯得如大海中的一葉孤帆一般,難以把握。
彼時的大唐王朝,早已行将就木。各地的藩鎮割據,内部的宦官專權,輔以黃巢起義的烈火,也讓這個王朝危如累卵。于是伴随着馮道的長大,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被曆代史學家稱之為“季世”的時代——五代十國時期。這一時期,強人輩出,朱溫、李克用、石敬瑭、柴榮、趙匡胤等人次第登場。至于百姓則多淪為草芥,易子相食的慘劇更是比比皆是。
身為文人的馮道,又是怎樣處之的呢?
從天佑年間被幽州節度使劉守光辟為掾屬,到此後曆任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官僚,在短短的五代十國幾十載内,他曆任四代十朝更是皆官至宰輔,時人更是贈“不倒翁”之稱号。
單從馮道的仕宦而言,不可謂不成功。然而,我們卻不得不說的是,在混亂的時局之下馮道的選擇顯然是與我國傳統儒家所宣傳的忠孝相悖。尤其是在宋朝理學興起之後,對于馮道這樣一位“多面人”被批評似乎也就理所當然了。
但平心而論,論迹而談,馮道能夠處于亂世而久居高位不倒,若非有大才大能,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而馮道的“才與能”,展現在平素為政上則為敢于直谏、務實。
在梁晉對峙時,後唐莊宗怒不可遏下令撤換郭崇韬另擇主帥,馮道則徐徐進言,這也令莊宗幡然醒悟;明宗時,面對明宗放縱享樂,他又諷喻谏之;此後他又不顧安危出使契丹,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即便身處高位,他卻能夠務實處之,提攜賢良,接濟群眾。
可以說,這些舉動都是他身在五代這樣一個亂世所給出的人生答卷。縱使天道有變,人生無常,但行好事足矣。
這也成為了他能夠寫出《天道》詩的緣由所在。
《天道》詩的寫就、分析
《天道》
(五代.馮道)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在這首詩中,飽經滄桑的馮道将一切歸為“天道”,但這種歸卻又不是消極避世的,而積極向上的。
他認為富貴貧窮是天意,但卻又不贊同消極待之。那麼要怎樣對待呢?無它但行好事,隻要能把握當下,做好當下就好。至于将來,就由他去吧。
世間的萬物皆有其中的道理,冰雪會融化、春草自會生長,一切總會水到渠成。這難道不就是馮道本人一生的寫照嗎?正所謂從道不從君是也。
身處季世,他并不能自主選擇;身為文人,他亦無力終結亂局;但身為一個人,一個曆仕四朝十帝的宰輔之臣,馮道又何嘗沒有自己的堅持呢?
而“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正是他的堅持所在。
小結
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口中的不堪之徒,筆下無數後人信奉的修身良言,就這樣有趣而不失诙諧地集于一身。
但我們更懂曆史所帶來的深邃意味,從時人口中的五代良臣到史家筆中的奸佞之輩,這莫不是時勢所造。
不過相信馮道如是泉下有知,知曉了歐陽修、司馬光诋毀之言,反倒應該不會太過怨憤吧。畢竟,這是一位“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的好人,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