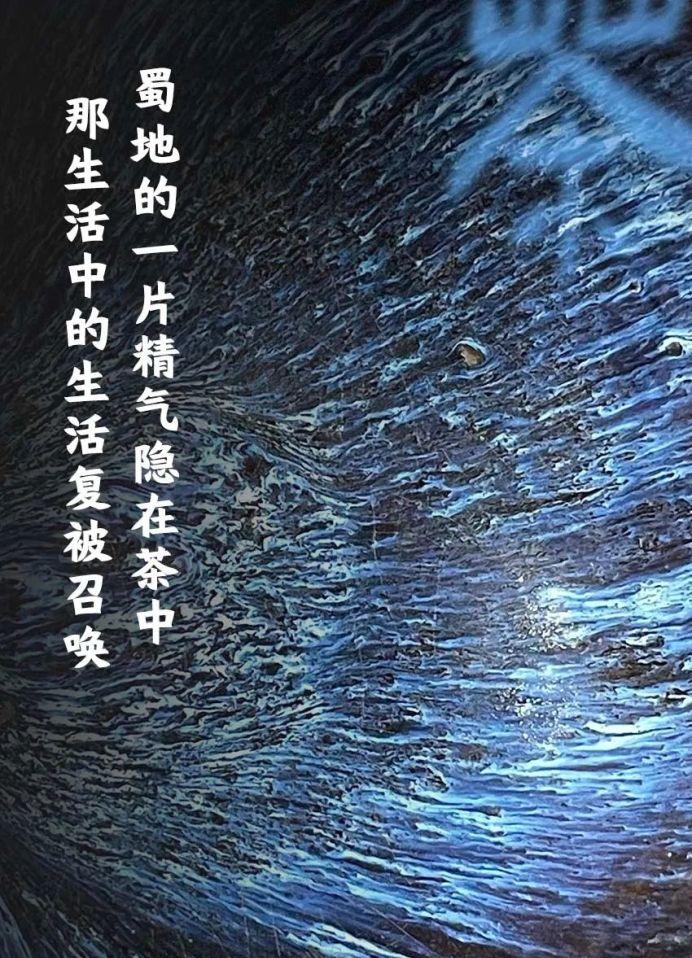
整理 / 和映龍 白郎
蜀地有陰翳之美,其中的一片精氣隐伏在至柔的茶中。蜀人喝茶之風久遠,宋代成都是蜀地茶生活美學的一個高峰。時光的虛空,宋盞的明暗,彙于琥珀茶湯;昔光中的記憶、氣息和滋味,依稀漂浮于幸存至今的宋代古器間。
美育家田野同時也是收藏家,對宋盞及各類古器有甚深研究。沒有美世界将墜入永夜,美是醒世之力,亦是有無相生之道,仿佛心田奔湧着無盡的甘泉,田野持有“無“的内證,也持有”有“的内證,這“無“是西方經典音樂,這“有“是東方古代器物,西方之美和東方之美的相攜,閃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純光。那生活中的生活複被召喚,2021年秋天,在田野每日隐修其間的藝術之宅,随筆作家白郎與他就川窯宋盞、宋風茶韻、個人收藏生活史、茶之東方審美等主題,進行了一場訪談。
▌雅集中的宋盞 白郎 攝
淡青茶煙裡一盞度千年
白郎:“茶”字拆開,人在草木間。我的一個感慨是,風雅宋代早已逝去,但若要追憶夙昔,留存至今的那些宋盞仍能穿越時空的淵面,呼出淳香茶氣。一盞度千年,舊物令人懷想,釉彩上的毫紋與光暈,仍能遙映出春宵飲抹茶的宋人姿影,淡青茶煙裡,啜英咀華,碧玉瓯中翠濤起。從個人收藏生活史的角度,田野兄還記得自己收藏的第一隻四川窯口的宋盞嗎?
田野:記得的,是2003年,當時每個周末舉辦的收藏品市集設在杜甫草堂北門外。我一次性買了3個,都是合川那邊塗山窯的,沒過多久又買了幾隻,有塗山窯的,也有清溪窯的。這是一種緣分,很個人化,我本人就是在合川出生的,是以對川東,尤其是合川,懷有很深情感。這幾隻古樸簡素的宋盞,讓我感覺挺親密,我和它們屬于同一片土地。
白郎:川窯出的宋盞挺豐富,回到盞器本身的審美上,你有沒有格外偏愛的窯口?
田野:宋代川窯比較重要的窯口,如邛窯系、廣元窯、西壩窯、塗山窯、清溪窯等,要探讨的話還是要具體到某一件器物某一隻茶盞,具體才會比較真實。比如我收藏的成都金鳳窯白釉盞,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束口,其他窯口的盞都有束口,但是你看這隻的束口,就像是拿着繩子,把它勒起來,這個勒的力量很深,是以束口就很清晰。這個感覺,就像是那年你去佛光寺看到的唐代鬥拱,猛地伸出來了3米多。當時我看到這個有點激動,雖然它是一個茶碗,當在各地窯口的宋盞中沒有伸出來那麼多的。而且上面既素雅又斑駁的開片極美,一派天成,這不是當時燒出來就有的,是漫長時間自然形成的。
白郎:在宋代成都的窯口裡,這麼有審美品格的白釉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在文獻資料裡,記載着川西地區從唐朝開始一直到南宋時期都生産白瓷。
田野:是的,成都宋代時期的白瓷,有很多種風格,比如說位于彭州的磁峰窯,所産白瓷比較清秀,雅且薄,燒制的溫度比較高。有些柴窯燒出來的白瓷品質不錯,薄如紙,色如雪,白如玉,聲如磬。因為我搞音樂,我對聲音是很敏感的。
▌宋代川西金鳳窯白釉束口茶盞
▌宋代四川塗山窯茶盞
▌宋代川西榮昌窯紫陶胎窯變盞
白郎:黑釉盞和青黑釉盞,當時好像很受追捧。
田野: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是個鬥茶高手,他寫的《大觀茶論》就說:“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為什麼要用黑瓷來襯托茶呢?因為當時的點茶之風比的是湯色和泡沫,追求茶味的香、甘、重、滑,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而黑釉恰恰是最好襯托白色的。宋徽宗實際上帶動了茶器的變化,福建的建盞,就幾乎隻燒茶盞。除了建窯,據我所知在全國那麼多窯口裡,隻有四川的廣元窯,出過一隻茶碗的碗底寫有“供禦”兩個字。
你再細看另外這隻黑釉盞,深腹束口,但是它這個束口就不像金鳳翔那麼厲害。雖然是束口,但是要松一點。這是我個人很欣賞的一個川窯的盞,榮昌窯。川東榮昌窯實際上有極精彩的茶盞,存量不是很多,名氣不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引起哪怕是四川收藏家的深入認識。
白郎:提到榮昌窯,感覺會不會和後世的紫陶有些淵源?
田野:對的,但不是近現代的紫陶,那些紫陶已經沒辦法從美學高度去探讨了,隻是一些産品而已,完全談不上美。我對榮昌窯有一個特殊情結,就是因為它這個紫胎,它的胎并不像廣元窯、西壩窯或者是我剛才說的金鳳窯,或者其它川窯,那些是化妝土畫上去的,但榮昌窯不是,它本身就是紫胎。中國有好幾個地方有紫陶的傳承,廣西的欽州,山西的平定,雲南的建水,還有就是四川的榮昌。
白郎:裡面也有你對紫砂的一個情感投射吧?
田野:是的,我對紫砂情有獨鐘,看到這種質感和顔色的胎,就會生出一種強烈的親切感,看這個東西的時候,内心被情感所籠罩,整個是浸透了的那種情感,再加上這隻盞的器型也很美。這個盞儲存了榮昌在宋代的質感和顔色,紫胎上面是一層白色化妝土,接着是一層深黑色的釉,然後上面再有一層釉,這釉上出現了藍色和白色的窯變,既微妙又豐盈。
白郎:什麼時候開始收藏四川以外的宋盞的?
田野:2007年,帶學生到廈門參加鋼琴比賽,我提前兩天到的,想先去古玩市場逛一逛,主要是去找老紫砂壺,在這個過程中碰到了一些建窯的宋盞。那一次沒買,但第二次去廈門,就買了一隻建盞,這是最早接觸對四川以外的茶盞,這隻建盞口徑隻有九厘米左右,上面還有兔毫。我發現玩收藏有一種地域性,說起來也是人性很自然的流露,就是很多藏家對當地窯口的情感很深,比如福建人,尤其是閩北人,對建窯的情感很深,成都人呢,對川窯的器物情感很深。我們沒法去要求外地人,對川窯也要跟我們有一樣的情感,這個現象是很普遍的。
白郎:在川窯産的宋盞中,你認為哪個窯口的成就最高?
田野:綜合來講,廣元窯的品質,在川窯的宋盞中是最高的,為什麼這麼講,首先是廣元窯當地做茶盞的胎土得天獨厚,整體上來說是四川最好的。把一隻茶盞放在手中,這個分量叫手頭,在整個四川窯口裡廣元窯的手頭是最重的,瓷胎的含鐵量和密度是四川其它窯口比不了的,在這一點上它接近于建窯,建窯的胎被稱為鐵胎,這是福建人引以為傲的,覺得建窯就是中國茶盞的代表。
▌宋代四川西壩窯茶盞
▌宋代四川清溪窯白釉束口盞
▌宋盞的靜光
白郎:在這點上,也可說有一種沉着的力量之美。
田野:可以這麼講。你看我現在手裡拿着的這隻廣元窯宋盞,廣元窯最吸引人的特質,它身上都有了,它是束口,盞身上布滿了兔毫,然後也有一圈燈草邊,燈草邊就是在茶盞口檐這個地方,有一圈黃顔色的釉,這個效果就像鑲了一個邊兒似的。不僅如此,這隻又有白色的化妝土,又有黑色的護胎釉,這些古法一應俱全于一盞上。拿到手上,它很壓手,整個盞生發出像生鐵那樣的氣韻。
白郎:宋風追求有純度的素雅,這種方向容易産生輕盈之美,輕盈很多時候會流轉為輕飄。但也有些輕盈之态,一旦和力量融為一體,就會産生輕與重交彙後的另外狀态,一種靈動與充實的合一,這隻盞就有這種美。
田野:它散發着很雅的氣息,在這個雅裡面,有厚重,一種緻密和堅硬的質感,像生鐵和岩石那樣,内蘊豐沛。
白郎:想聽你聊聊與自己最有緣分的一隻宋盞。
田野:我最近六七年用得最多的一隻盞,是塗山窯的。就我個人内心而言,雖然在成都多年,但我是把自己看成川東人的,覺得身上有巴人的某些東西,是以呢,這種私密情愫自然投射到了器物上,塗山窯可以說是川東最大的窯口,我的這隻很特殊,好像單獨達到了為它而生的一個美學層面。盞型上,它屬于深腹和束口,隻是束口微妙,因為不是很明顯,不認真看,可能意識不到它是束口的。我看了很多器型之後,再去看它,經常會被感動。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外面有一個黑色釉滴。我剛買到的時候,給它取了個名字,就一個字——“淚”。我後來發現千利休,他自己做了一個茶勺,名字也是“淚”。這是有趣的巧合。塵世間歡樂的淚水、悲傷的淚水盡在這一盞茶湯裡,悲欣交集啊。黑釉滴周遭是紫金釉,唯有此處,是黑如漆的一滴淚滴下來。這隻盞與我相伴,我出差到哪兒,都随身帶着。
白郎:這隻盞,确有一種秋潭洗神的古韻。記得有一年你去了大理,這裡的地脈辨別,有“風花雪月”之說,你帶去了一個宋代碟子,碟面上有“風花雪月”這四個字,在洱海的千頃碧波畔,這太浪漫了。
田野:那次我們全家是跟着朋友林子去的,他老家就在大理一帶。除了洱海,林子還帶我們去了雞足山,在雞山瓊樓峰崖壁間的華首門,我倍感一種迥異的壯闊氣場,當時那兒站了很多人,比較嘈雜,走近那扇天然石門時,我把手放在褐色岩壁上,一種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感受百轉千回,一下子彙聚過來,非常感動,眼淚不禁流下來了,沒想到的是,我往前走兩步後,發現下面有塊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寫着“淚泉”,旁邊是從岩壁裡滲出的很細泉水。而我正好帶着塗山窯的 “淚”盞,它就在我随身背着的包裡,在我背上。
▌宋代塗山窯紫金釉茶盞——“淚”
▌宋盞與春花
▌古凳上的宋代四川廣元窯茶盞
宋代川窯的南方民間調性
白郎:當從審美角度來探讨川窯的宋盞,金鳳窯在成都區域的宋盞裡,算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了,對吧?
田野:嗯。能接觸到的金鳳窯宋盞,實物較少,成都博物館有幾個,但是它有特質,讓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金鳳窯的。金鳳窯的一些盞,可以說是宋代川窯黑釉茶盞裡器型最大的,而且有特别亮的金屬般光澤。除了今天大邑的金鳳窯,彭州的磁峰窯也出茶盞,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鬥笠盞。
白郎:蜀地自古飲茶之風很盛,兩宋時,川窯出宋盞的代表性窯口,還有哪幾個?
田野:不少,比如西壩窯,廣元窯,塗山窯,還有清溪窯。自古以來,陶瓷器基本上是就地取材,這就造成了胎土和釉色的差別。西壩窯的胎土,相對比較疏松,塗山窯有意思,裡面既有那種比較粗的砂,但也有比較細的,甚至有很細的。而最細的是清溪窯。從胎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川窯裡面最細膩的——我還沒有說細密——這是兩個概念,細密呢,還有一個密度在裡面。從清溪窯的細膩來講,這幾年,有人給它安了一個名字,叫類汝似鈞。我個人不認可這個提法,宋代五大名窯官、哥、汝、定、鈞,其中汝為魁首,清溪窯跟中原的汝窯離那麼遠,其實沒有什麼關系,這個提法是想從那兒沾點光。
白郎:說到這兒,我縱深一句。就整個宋代瓷器版圖來說,川窯好像一直以來不被重視,有一種很邊緣很民間的感覺。
田野:這其實是一個有意義的、值得拿出來專門探讨的問題。為什麼相對于那些影響大的窯口,比如建窯,比如吉州窯,川窯的名氣和影響沒那麼大?其實從美學來講,川窯出的一些精彩器物不次于這些名窯。建窯的東西,現在綜合來講是天下第一,到目前為止,宋盞的拍賣紀錄都是建窯創造的。油滴盞,本來是日本的臨宇山人收藏的,被我們國内的一個老闆買了。多少錢?7800多萬人民币啊!一個12公分左右的油滴盞為什麼賣那麼貴?首先這是日本的一個大美學家臨宇山人的藏品。這個人是日本近百年來最厲害的收藏家之一,美學眼光極高,這是他收藏的,還有一點,這隻盞确實品質很高。從美學來講,就我個人的審美體驗來講,它是很珍貴,而且傳承有序,代表了建窯的最進階狀态,但是,審美是有很多真實層面的。建盞往往有一種殿堂感,一種身份感,廟堂之氣,高高在上,顯得很嚴肅,你面對它,它好像闆起個面孔,就像音樂家裡面的巴赫。從建窯那兒,我覺得自己沒有感受到一種深切的溫暖。但是川窯有這種溫暖,川窯除了具備建窯有的兔毫,而且兔毫中還有金兔毫、銀兔毫、藍兔毫。川窯裡的有些茶盞,對我來講,一種純真之氣撲面而來,甚至是童真,就是稚拙,把純真跟古拙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美學體驗,川窯茶盞帶給我很深的感觸,四川曾經燒出過這樣的茶盞,我覺得很榮耀。
審美與市場并不一緻,比如說家具,最近這些年在家具的審美上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過去很多年,我們可以稱之為唯材論,就是說材質是決定性的,連王世襄,我覺得都算是這個唯材論裡面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收藏的重器,大都是黃花梨和紫檀家具。王世襄晚年時,曾感歎說如果自己再年輕二十歲,要把時間全部用來研究柴木家具,因為,那又是另外一個世界,蘊藏着更高的美學高峰。是以,唯材論實際上是有很多局限的。
▌田野監制的紫砂壺及收藏的紫砂古壺
▌田野監制的紫砂壺
白郎:很多事,實際上是話語權的問題。秦漢以來,四川離權力中心要遠一些,區域文化中有一股自成一格的南方民間自由調性。其實器物背後站着的是人,是以,人的生命狀态會顯現在川窯的器物裡。
田野:川窯在名氣上現在沒有建窯或吉州窯大,與四川是在内陸幹系很大。日本人所崇拜的唐物,從美學上講,其中也有一些東西并沒有那麼了不起,但他們照樣崇拜得很,由于種種條件所限,他們那時隻能接觸到這些東西。日本草庵茶的開創者村田珠光做過幕府将軍足利義政的大茶頭,他有一個福建洪塘窯的茶入,即著名的九十九發茄子,洪塘窯茶入在宋代就燒出來了,日本人是從明代開始玩的,而且玩出了那樣一個狀态。由于福建還有江西方位偏東,比較容易運到日本,四川離得很遠,就很難。如果四川離得比較近,那今天川窯的曆史就不是這個曆史。
成規模成系列收藏茶盞的,在宋代以前是幾乎沒有的,從宋代開始有了,為什麼?皇帝喜歡玩這些東西。宋徽宗就是鑒賞家,他的影響很大。以前,收藏家有各種各樣的,比如說收藏青銅的,所謂的“吉金”,但是幾乎沒有人專門收藏茶盞。現在為什麼有?還是因為日本,因為日本對這個東西不僅有傳承有序的研究收藏,而且茶盞在日本影響極大,當成國寶來崇拜,有很高經濟價值,比如說有隻宋代曜變盞,在100多年以前就相當于東京1000多套别墅的價值。但是日本人沒有機會接觸到川窯,川窯的東西在日本沒有形成影響力。川窯的東西,哪怕有那麼幾件在日本某一個比如像足利或者是村田珠光、織田信長這樣的人手上,或者是在寺院裡收藏有這樣的器物,那川窯的名氣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這個問題簡單說來就是這樣。
白郎:在川窯裡,邛窯的很多器物,吸附着一股離山水很近的無邪之氣。邛窯的三彩在唐宋時代還是有影響的,很獨到。
田野:過去很長期間,對邛窯的認識是有限的,也不太重視。邛窯在陶瓷史上的地位是比較重的。民國時,軍閥唐式遵組織人手大肆挖掘邛窯遺址,挖了很多邛三彩賣給老外,是以邛三彩在外國影響不小。
▌風雅宋碗 田野 攝
▌宋代西壩窯窯變瓷 田野 攝
▌川西宋代玉堂窯異形磁碗
▌宋代銅花插
白郎:有種觀點認為邛窯與長沙窯是姊妹窯,從長沙窯的器物看,很多審美上的自由意趣、風格,包括燒制方式,跟邛窯是一脈相承的。但長沙窯也有自己的顯著特色,比如說在瓷器上題寫詩作。
田野:這有一個先後問題,邛窯在前,基本上是姐姐,而長沙窯是妹妹。是邛窯影響了長沙窯,這樣的話呢,後起的長沙窯更細膩,更精緻,裝飾手法上也更豐富。除了你提到的在器物上書寫詩歌,還在器物上貼塑。
白郎:在宋代川窯中,樂山西壩窯出産的各種盞數量大,這個窯口和江西的吉州窯在很多方面也挺接近。
田野:吉州窯是當時南方規模極大的一個窯口,品種豐富。而西壩窯是我們四川宋窯中的一個大窯口,綿延五公裡。西壩窯有很粗的東西,窯溫不能燒太高,一旦燒高就會出現裂痕和起泡,因為當地的疏松胎質吃不了高溫,可能八九百度就不行了。西壩窯這種東西很多。但西壩窯有極精的東西,窯變斑斓,它向吉州窯學習,又有自己的特點。吉州窯的枯葉天目是這個窯口特有的,還有一種被人稱為“黑妞”的盞,有人說黑妞才是吉州窯的最高代表,吉州窯的正窯口永和大窯才有這種東西,把它斜着放也能自己回正,重心很低,它有吉州窯特有的卧足,上面薄下面厚,是以造成這種情況。
白郎:與漢唐時期一樣,宋代成都是一大都會。宋末時,四川的人口已達1000多萬,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戰亂,人口銳減到了80萬多人,原有文化被嚴重摧毀。比如說大慈寺,寺裡從唐代延續到宋代的1萬多幅壁畫全毀了。曆經這次浩劫,四川的許多特色性區域文化,盛況不複。當然到元代,還是有一些窯口在繼續燒制,像剛才說到的西壩窯。
田野:元氣大傷。元代時,除了西壩窯,廣元窯和塗山窯等仍然有一些延續。
▌四川安嶽宋代紫竹觀音造像 白郎 攝
▌2010年,老萬年台旁的川西鄉村茶館 白郎 攝
▌宋代四川僧人牧溪的六柿圖
▌按牧溪六柿圖擺放的宋代茶盞
煎茶抹茶取深清
白郎:揚之水在《兩宋之煎茶》一文中說,“煎茶與點茶,均是兩宋時代的飲茶方式,前者是将細研作末的茶投人滾水中煎煮,後者則預将茶末調膏于盞中,然後用滾水沖點。站在宋人的立場,似乎可以說,煎茶是古風,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在詠茶之作裡已經說‘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煎’。今人考察兩宋茶事,也認為點茶早是這一時代普遍的習俗。與陸羽《茶經》講述煎茶法不同,宋人茶書,如蔡襄《茶錄》、宋徽宗《大觀茶論》,所述均為點茶法。曰兩宋點茶盛行,誠然;然而與此同時,傳統的煎茶之習卻并未少衰,檢點付諸吟詠的茶事,這是一個清楚不過的事實,而繪畫作品、出土器物,也可以成為它的佐證。”這段話闡述了兩宋時期,點茶法與煎茶法并行的情狀,隻不過點茶是新風,煎茶是古風;宋代時成都人的日常飲茶風尚,想必也是如此。
田野:雙流那邊有個地方頗有古意,叫煎茶鎮。從現存茶器上看,比如說廣元窯有很多茶盞,明顯有使用過的痕迹,而且是旋轉的痕迹,應該是用茶筅打出來的,而茶筅是宋代點茶中的抹茶工具。
白郎:從人文地脈的角度,成都平原的地氣多陰翳,陰則靈氣往來,并沉積出自成一格的生命美學,其中有一股平民精神式的根氣,猶如離土地離市井很近的竹枝詞,升騰着民間林盤般的片片光暈。當然也有純雅的細部,比如蜀錦、蜀琴。大俗,大雅,相通的,這兩種氣實際上是在激蕩,在傳遞,在互濡,在湧動和流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哦。
蘇東坡有一首詩是關于煎茶的,叫《汲江煎茶》:“活水還須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做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蘇東坡其實和成都因緣很深,有這麼一則野史,他出生前,他父親蘇洵到過成都玉局觀,成都十二月市的藥市就是在這附近舉辦的,在觀裡,蘇洵看到一幅畫,覺得跟這幅畫有緣分,就用手上的玉換了這幅畫帶回去,過了一段就有了蘇轼和蘇轍。後來,被充軍海南的蘇東坡65歲時,皇帝照顧他,給他一個閑職,讓他回成都做玉局觀的負責人,蘇東坡很高興,覺得這個職務有歸宿之感,沒想到在途中就去世了。我提蘇東坡是想說他和蜀地的緣分,他在生活美學方面被視作一個典範,你對蘇東坡有什麼看法?
田野:主要是感受他豐盈的那種生命狀态,在坎坷命運裡,仍然松風竹爐提壺相呼。對我來講,因為喜歡紫砂,是以印象最深的是蘇東坡和宜興的淵源,原來有疑問,為什麼在太湖之濱的宜興會有一個蜀山呢,後來才知道,是他曾在那兒任職,本來那個地方叫獨山,他說此地似蜀,就把反犬旁去掉,改稱蜀山了。
白郎:說到抹茶,2017年咱們一起去鐮倉建長寺時,寺裡的主持吉田長老,以日本的抹茶招待我們,記得披着清光的黑盞裡,茶湯上端浮着一片粘稠的青碧茶沫,雙手捧起來喝,茶清新的鮮腥味直抵深喉,問我們以前可曾喝過,回答說沒喝過,長老于是笑道:“這可是你們的祖先,宋朝人的喝茶方式呀,傳到日本後,經過改良一直保留着。”當時,田野兄帶了六隻宋盞,你用宋盞泡普洱茶來請大家喝。
田野:那次帶去的川窯宋盞,基本上是塗山窯的,也帶了那隻“淚”。
▌日本茶聖千利休使用過的井戶茶盞
▌村田珠光曾使用過的珠光青瓷盞
▌日本茶室中的挂軸
白郎:那次日本之行,咱們的翻譯日本學者鈴木博之是神戶人,他說在他們老家一帶,春天秋天冬天這三季,家裡主要喝煎茶,夏天時喝麥茶,有貴客來的時候,會做抹茶。
田野:就抹茶來說,實際上在日本也有很多流派。僅僅千利休這支就有好多門派,什麼表千家、裡千家,等等。但是日本一些茶禮是從宋代傳過去後就一直沒變過的。
白郎:在宋代成都的茶文化與日本茶道之間,成都高僧圓悟克勤值得一提,日本禅宗的二十四個派别,有二十派都是出自于他的傳承法系,他的墨寶圓悟印可狀是日本茶道的至尊之物,這件墨迹實際上是前半部分,一休宗純将其傳給了弟子村田珠光,也就是草庵茶的創始人,幾十年間,村田珠光一直在參悟這張印可狀,去世前,給徒弟說自己去世後,每逢他的忌日,記得把圓悟印可狀挂出來,然後用他喜愛的茶盞泡上茶。禅茶,是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村田珠光寫過一篇對茶道影響很大的《心之文》,裡面有一句話“莫以心為師,成為心之師”,對這一句,你是怎麼解讀的?
田野:我其實很喜歡引用這句話。對于我來講,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很強烈、很鋒利的一種狀态。有一個問題,成了現代人的一個夢餍,就是越來越多地使用頭腦,依賴頭腦,是以心性衰減。古人講哀莫大于心死,心性衰竭了,這個生命實際上就是行屍走肉。“莫以心為師,成為心之師”,意思是讓我們最大限程度地回返生命的本源,回到做主的心源狀态,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太容易用語言把它說得很清楚,我自己看到這句話以後,好像寒毛都豎起來了。這句話運用出來,類似于出自直覺的一種渾然狀态,不要分析,不要以頭腦的方式思慮,将其融進對器物的審美,是一種本自如此的活潑與渾然。
白郎:講得精彩。想起闡述審美精神的一個句子:“削減到本質,但不要剝離它的韻,保持淨潔,但不要剝奪生命力。”
田野:平常我也在做音樂美育,現在很多人把音樂搞成一門知識來對待,像這樣學,就算去到所謂的最高學府,茱莉亞也好,柯蒂斯也好,如果把音樂當成知識,就永遠在音樂之外,在音樂的核心之外。從外往裡面走,永遠走不到那個地方。必須要把音樂當成知識的這種概念全部抛棄掉。可以說,削減就是首先要把知識削減掉。要以聲音為法門,這樣的話,這個聲音将會把我們帶到作品的核心。
白郎:音與聲相合,這個聲音,或者說音樂性的能量,在宋代四川的茶盞裡,是不是也顯現無疑?因為當這隻盞彌散着靈動的“音樂”時,它就有審美品格,也就是樂變成了韻。
田野:我現在看器物,一定會去體會它的韻,同時呢,我的耳朵聽到它化成一種語言在向我訴說,看到不同的東西就有不同的語言再向我訴說。我覺得真正要感受音樂,首先從方向上,就不能是從外往裡去進入,而是一開始就在這個核心的内部,然後從中心往外去感受。
▌京都岚山桂離宮
▌京都銀閣寺東求堂 白郎 攝
▌青黛林中的日本佛寺 土門拳 攝
不懂音樂的美育家不是好茶客
白郎:雖然原有的生活傳統已中斷,但今天仍然有很多可能性。成都人自古就在生活美學方面有獨到之處,在今天,仍有各種各樣的飲茶風尚在這座城市彙集。在茶這門生活美學的背後,實際上存在着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內建,時光的橫切面如果隻有“今天”,沒有了“往昔”,那“今天”有可能淪喪為某種廢墟之場。值得欣慰的是,今天仍有很多人在學習宋風,學習宋人的飲茶美學,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田野:就我來講,覺得凡是關乎美學的,都是個人行為。個人行為才是真實的。一旦要把它推廣,或者搞成社會風尚、社會行為,那它立馬又變成虛假,變成各種幻象。是以在這一點上,我個人既不悲也不喜。我覺得這隻是個體生命的一些真實體驗和感悟,他在這個感悟裡,繼續去追尋。今天可以看到各種茶空間,各種應運而生的茶人,他們很活躍,舉辦茶會,然後相關的一系列産品也應運而生。這些跟我心中要追求的,不是一個脈上的東西。越來越多人的喝茶,各種各樣的茶器也越來越多,表面看是很繁榮,實際上,恰恰是一種荒蕪。就像宜興的紫砂,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可以說是自有紫砂壺以來最繁榮的時期,但從器物審美的氣息和精神内質來講,這是一個荒蕪、異化的低谷時期。
白郎:宋盞、宋器,這些年來一直環繞着你,宋代氣息對你個人有什麼啟示?
田野:收這些茶盞真實地豐富了我的審美,這個豐富指向的是一個“一”,是一個更渾然更純粹的“一”的狀态。實際上,宋代對我來講是很遙遠的狀态,但這些器物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美,這對于我是如此真實,我把這種美跟其他的美,包括音樂的美,融合在一起,這是對我這個生命的滋養。至于說到喝茶本身,是很随意的,我根本就不認同那些表演性的東西,覺得那毫無意義。
▌金代(相當于南宋)菩薩造像 白郎 攝
▌奈良唐招提寺的淨池 白郎 攝
▌日本鐮倉明月院 白郎 攝
▌雲煙幽壑 金農 作
白郎:“劫火洞然毫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這是日本煎茶道祖師賣茶翁的句子,煙霞橫呈,知道你欣賞他。
田野:遍浮山林氣的賣茶翁,我是非常欣賞的。千利休創立的更有儀式感的抹茶道,随着時光的流逝,往往成為身份的标記,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儀軌,包括茶席的尺寸,器物的顔色、形狀,等等,後來出現賣茶翁這麼個特立獨行的人,他對自由的追求,是對各種束縛的叛逆,也是對茶道的修正。
在審美這一塊,我是有很準确的情感定位的。什麼叫情感定位,這是我發明的一個詞。我曾經思考過一個問題,既然每個人的經曆不一樣,性格不一樣,情感不一樣,很多時候每個人聽的感受也都不一樣,但演奏家有無比強大的情感定位在他心裡,也就是說他彈每一個音,每一個段,都有具體真實的情感體驗在那個地方。後來,我把這個觀念,很自然地就轉移到了器物上,就是我看一個器物時,我仿佛能感受到它的韻律和圍繞着它的聲音,然後也會出現情感定位。對于我來講的清晰,跟别人的清晰是不一樣的。大多數人的清晰就是拿着放大鏡來看清楚一個東西,但是,對于我來講,我要的清晰不是這個,我要的清晰是什麼?用同樣的放大鏡,把陽光聚集起來,把這張紙點燃,燒成灰燼,這個是我要的清晰。因為在音樂和器物的美學體驗裡面,一般性的那種清晰是遠遠不夠的。那種清晰,到了某一個層面的時候還是會變得模糊。是以你必須有這種狀态,就是你把它燒化,實際上是發生了另外一個新現象。當你有這種清晰的時候,所謂目光如炬的狀态,你才能夠更深地把事物的本質提煉出來。這就是我要的清晰。
▌音樂是田野的另一股精神甘泉 田野攝
▌美育家田野
白郎:你跟别的美育家有明顯差别,學兼中西,并在音樂上有強大體證,感覺那麼多年來,你把在音樂方面的修為,投射到了古器物上,形成很多自己的獨到眼光和審美觀念。具體到茶文化跟音樂之間的關系,請談一下。
田野:我們今天大部分時間是在探讨茶器,尤其是川渝地區的茶碗,但實際上不要忘了,這些茶器,不管是普通的,還是有極高美學品相的,它們都是來盛茶的。實際上茶是起決定性的,茶器的變化,也是随着飲茶風格和方式的變化而不斷在變化的。相對來講器物是看得見摸得着的,但它承載的這個茶湯,岡倉天心所說的那一碗人情之湯,這個東西,這個味道跟音樂的關系更緊密。因為音樂是聽覺的藝術,聲音的藝術,而喝茶是用味覺。這個味覺,它這種向外的開闊,向内深入到内心深處的幽玄微妙,更接近于音樂,是抽象的。有些時候,這個味道給你一種很絕妙的感覺。我喝很多年以前買的一款普洱茶,一口下去頓生百千感動,覺得雲南的那片天地,藍天、白雲和紅土,還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雲南人,那種雲之南的淳樸之氣,全在這碗茶湯裡面!這個感動是多層次、立體的,把我籠罩。
白郎:不論是宋代還是今天,在生活美學範疇裡,自由的能量,慈愛的能量,美的能量,力量的能量,都是主脈,具體運轉各有造化。顯然你在音樂中凝聚了這幾種能量,如果讓你拿着自己叫“淚”的心愛宋盞,穿越時空傳回宋代,你會選擇哪個地方?
田野:按照我的本性,應該還是四川,川東嘉陵江流域。
白郎:今天的談話已挺豐富了,打個總結吧。有句話說得好:“大地的秘密力量,是唯一的現實”, 以宋盞為由頭,我們聊了很多,其實是圍繞這個軸在縱深開來。
▌2017年春,田野、白郎在京都落柿舍
整理 | 和映龍 白郎
供圖 | 田野 白郎
主編 | 晨曦
責編 | Jamie
美編 | Birdy
【讀城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