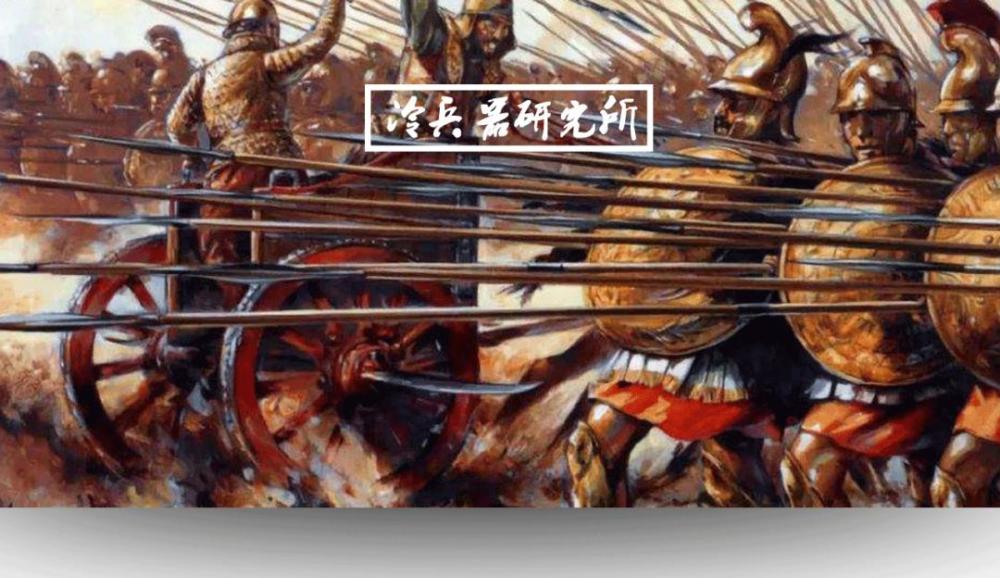
編者按:從波斯人與希臘雇傭軍交手的庫納克薩戰場(公元前401年),到本都軍隊與恺撒對壘的澤拉之戰(公元前47年),鐮刀戰車——其名稱源自車軸兩端長約1米的巨型鐮刀——在中東地區盛行了将近四個世紀。它始于波斯帝國,馳名于亞曆山大與大流士的高加米拉會戰,其後又在塞琉古帝國和本都王國得到了頻繁運用。作為古典時代的“重型坦克”,它往往能夠摧毀敵方步兵的密集隊形,帶來嚴重的生理和心理創傷,制造極大的恐慌。當然在國内網絡上,“受累”于先秦時代的中國也大量使用戰車,是以這些鐮刀戰車也算是風評被害。因為總有一些人試圖證明鐮刀戰車是一種大而無當的武器,然後形成一種從西到東的鄙視鍊之類。那麼,曆史上這種武器到底是大而無當,隻能充當鄙視鍊背景闆呢?還是古典時代的重型坦克?
古代世界的重型坦克——鐮刀戰車
聽說那鐮刀戰車的利刃時常在混亂屠殺中驟然撕裂四肢肢體離開軀幹墜落地面而飛快傷害帶來的疼痛思想和意識仍不知曉——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物性論》
▲飛馳的鐮刀戰車
起源
記載鐮刀戰車最為熱心的古典作家要數色諾芬,作為最早與這種新式兵器交手的希臘人之一,色諾芬不僅在自傳《長征記》、史書《希臘志》中給出了它最初的幾份實戰記錄,還在政治教育著作《居魯士勸學錄》裡,煞有介事地講述了波斯第一帝國開國君主居魯士大帝發明鐮刀戰車的故事:“他(居魯士)改換了那種特洛伊人先前使用的戰車,代之以一種更加合用的戰車,這種戰車的車輪十分堅固,可以經受颠簸,同時,由于采用了長軸,也使寬大的底盤更為結實,而馭手的座位則移至一個可以叫做高台的東西上,這個高台用硬木打造,延伸到戰車的前沿,在車身闆的上面還要留出一塊地方讓馭手駕馭戰馬。馭手全身護具齊全,隻有兩隻眼睛露在外面。他在戰車兩側的輪毂上還安裝了工匠打制的一種兩肘尺(約為1米)長的鐮刀,還有一種則安裝在木制車架底下,朝向下面,以備不時之用。居魯士發明的戰車型制就是如此,這種型制的戰車至今在波斯帝國的臣民當中還在使用。”(色諾芬,居魯士勸學錄,VI,1,27-30)
▲波斯帝國早期的戰車模型
盡管色諾芬對鐮刀戰車的技術特性給出了頗為細緻也較為準确的描述,但正如西塞羅所說,“色諾芬講述居魯士并非源于曆史目的”,這部基于曆史題材的政治著述出于教育目的,将諸多作者所處時代的波斯風俗習慣乃至器物歸結到主人公居魯士大帝的身上。事實上,哪怕是在大流士和薛西斯遠征希臘時期,也沒有任何有關鐮刀戰車的可靠記載。希羅多德曾經不厭其煩地詳述波斯帝國各地特色兵種——其中還包括印度藩屬的野驢戰車和利比亞藩屬戰車,但鐮刀戰車始終未曾出現在《曆史》當中。
▲大流士一世乘車出獵
據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曆史科學博士涅費德金(Нефёдкин)考證,鐮刀戰車實際上應當出現在阿塔薛西斯一世統治時期(公元前465-424年),它是兩次遠征希臘失利後,波斯帝國應對希臘式密集重步兵隊形的産物。
戰術特征
中東地區原有的普通戰車在戰鬥中的作用主要依靠車載戰鬥人員的發揮,它們往往會在步兵交戰前進行戰工廠中的房間的戰鬥,在步兵交戰時負責掩護己方戰線側翼,步兵交戰結束後展開追擊或抵禦敵方戰車追擊。隻有在敵方沒有戰車或敵方戰車已被逐出戰場時,才會偶爾正面攻擊敵方步兵。
▲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的中東戰車
▲亞述戰車浮雕
鐮刀戰車的戰術職能則與它的先輩截然不同,它完全取消了車載戰鬥人員,僅僅保留披甲馭手,是以,其殺傷力完全源自從車軸伸出的鐮刀和戰車本身的沖擊力。若是面對來去如風、隊形松散的輕步兵或輕騎兵,鐮刀戰車當然很難發揮作用,甚至可能在對方的投射打擊下幫上倒忙。于是,它幾乎唯一的作戰方式就是在适合馳騁的平坦戰場上沖擊缺乏得力投射兵種輔助的重步兵叢集。接下來,我們可以從古典文獻記載中逐次探究鐮刀戰車的戰術表現。
庫納克薩會戰(公元前401年):此戰是波斯王子阿塔薛西斯(日後的阿塔薛西斯二世)和小居魯士争奪王位之戰,小居魯士手頭的王牌是10400名希臘重步兵和2500名希臘輕盾兵,此外也有20輛鐮刀戰車。阿塔薛西斯的兵力要雄厚的多,但他最倚賴的仍是150輛鐮刀戰車。狄奧多羅斯指出“阿塔薛西斯在戰線正面部署了許多鐮刀戰車”,普魯塔克則認為“阿塔薛西斯将最強大的鐮刀戰車部署在正對希臘人的位置上,為的是在近接戰鬥前利用戰車的沖擊力分割(希臘人)的隊形”,色諾芬則在《長征記》中提到“他們(阿塔薛西斯部)前方是所謂的鐮刀戰車,彼此之間留有一定間隔……其意圖為直驅希臘軍陣并割裂其隊形”。可見,無論是小居魯士方的傭兵頭目色諾芬還是阿塔薛西斯方的禦醫克忒西阿斯(狄奧多羅斯和普魯塔克的記載歸根結底都源自此人的《波斯史》),都充分意識到了鐮刀戰車針對密集重步兵叢集的戰術作用。
不過,決定戰争勝負的主要因素終究還是人。希臘人的戰争藝術同樣在此前數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争中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戰術方面,重步兵的裝備不斷強化,輕盾兵的戰術地位也一再上升,單純的重步兵叢集逐漸退出曆史舞台。而在經驗方面,參與此戰的希臘傭兵幾乎都可說是百戰餘生的勇武老兵。此時的波斯人卻遠非如此,正如色諾芬所述:“那些(波斯)指揮官對戰車士兵竟然滿不在乎,反倒自鳴得意地認為沒有經過訓練的人也能夠像那些經過訓練的人一樣達到目的。這樣,戰車士兵倒是可以草草速成了,但這種人甚至還沒有沖到敵軍陣前就有一半已經倒在自己的戰車裡,另外一些則會自行跳出戰車。那些小隊沒有了駕馭戰車的人,因而對自己人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了對敵人的傷害。今天的這些波斯人……總是想要放棄戰鬥……必須依靠希臘人的幫助去面對敵人。”(色諾芬,居魯士勸學錄,VIII,8,24-25)
庫納克薩的戰況正是如此,希臘傭兵在雙方戰線相隔3-4斯塔達(約500-700米)時對當面對手發起沖擊,他們還用長矛敲擊盾牌以吓唬馬匹,一時竟吓得當面波斯軍隊敗陣逃跑。鐮刀戰車部隊既沒有加速沖擊空間,更因為馬匹受驚和馭手缺乏訓練而陷入混亂,竟然紛紛棄車逃跑,失去控制的鐮刀戰車有的在己方隊列裡制造慘劇,有的雖然沖向希臘傭兵隊列,也迫使希臘人閃開缺口,卻沒有己方部隊能夠跟進利用戰機。由此可見,庫納克薩之戰的确證明了鐮刀戰車對付重步兵的戰術職能,但波斯軍隊當時的糟糕人員素質則導緻它難以發揮作用。
▲庫納克薩時期的鐮刀戰車假想圖
達斯基裡昂戰鬥(公元前395年):此戰交戰雙方為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和波斯的弗裡吉亞行省總督法那巴佐斯,當時,已經取得希臘霸權的斯巴達派遣國王阿格西勞斯于公元前396年率領2000名“新公民”和6000名同盟軍前往小亞細亞開疆拓土。根據色諾芬在《希臘志》第四卷第1章中的記載,公元前395年冬季,趁着希臘士兵在弗裡吉亞首府達斯基裡昂附近分散搜集糧秣之際,法那巴佐斯指揮2輛鐮刀戰車和400名騎兵發起攻擊。希臘人見勢不妙,看到波斯戰車和騎兵向他們迫近,便趕緊集合成一個約有700人的密集陣。但法那巴佐斯當機立斷,将戰車置于最前面,他本人和騎兵跟随在戰車後面,随後下令向希臘人進攻。戰車突入密集的戰陣,将希臘人沖得七零八落,騎兵則快速跟進,殺死了大約100名希臘士兵,其餘人等則逃回營地。作為一場波斯人以少勝多的“翻身仗”,達斯基裡昂戰鬥充分說明了優秀的指揮官應當如何運用鐮刀戰車。首先,法那巴佐斯實踐了兵貴精不貴多的原則,僅僅400名騎兵和區區2輛戰車可以相對容易地完成兵種協同。其次,襲擊的突然性,使得希臘人沒有時間建構配備一定投射兵力的完備戰線。最後,鐮刀戰車充分發揮了它的突擊威力,在騎兵尚不具備撕裂希臘步兵密集陣能力時,充當了後世的重騎兵角色,破壞了希臘步兵隊形,令他們在面對跟進的波斯騎兵時門戶大開。
▲波斯騎兵與希臘步兵的戰鬥,公元前4世紀
▲持矛的波斯貴族騎兵,公元前4世紀
高加米拉之戰(公元前331年)
對陣雙方大流士和亞曆山大已經毋庸贅述,阿裡安、庫爾提烏斯·魯夫斯和狄奧多羅斯提供的古典史料,也使得高加米拉成為鐮刀戰車記載最為豐富的會戰。數十年來的勝敗經驗已經令波斯人意識到騎兵與戰車配合的重要性。根據阿裡安的記載,波斯大軍左翼前方部署了塞種騎兵、1000名巴克特裡亞騎兵和100輛鐮刀戰車,右翼前方部署了亞美尼亞、卡帕多西亞騎兵和50輛鐮刀戰車。不過,中軍前方的50輛鐮刀戰車雖然應當有戰象配合,但實戰中可能并未如此行事,大約是害怕大象驚吓己方馬匹。庫爾提烏斯·魯夫斯和狄奧多羅斯還指出大流士着手強化戰車武備,在車轅和車軸末端加裝了長矛和更長、更寬的鐮刀。
按照古典時代的傳統,馬其頓軍的左翼相對薄弱,這一翼配屬的輕步兵也僅有一些克裡特弓箭手和來自亞該亞的傭兵,這樣的投射火力似乎還不足以阻擋鐮刀戰車和騎兵的協同作戰。根據庫爾提烏斯·魯夫斯的記載,波斯右翼的50輛戰車在戰前特地平整過的戰場上朝着馬其頓左翼全速沖擊,其後又有1000名騎兵(狄奧多羅斯說是3000名騎兵)适時跟進。結果“有些馬其頓士兵被遠遠伸到車轅前方的長矛撕碎了,另一些被戰車兩側朝下的鐮刀撕碎。馬其頓人非但沒有逐漸退卻,反而散亂地潰逃,令他們的隊列陷入混亂”。此後,波斯右翼騎兵甚至突入馬其頓營壘,一度奪占辎重并救出大流士的家眷。之是以馬其頓左翼會陷入如此慘劇,顯然也是源于緊随其後的波斯騎兵密切配合戰車:他們既可以殺傷馬其頓方面的輕步兵,減輕戰車損失,也能夠利用戰車打出的缺口,将馬其頓步兵的後退、躲閃轉化為潰敗。
狄奧多羅斯的記載生動描繪了鐮刀戰車的殺傷效果:巨大的沖力和轉動的利刃,使得馬其頓的很多士兵喪命,造成的傷勢更是形形色色。鋒利的刀具和強大的力道,使得撞上的東西都被它斬斷,包括很多手臂、盾牌、武器和其他的裝備,還有不少的例子是頭顱被從頸部快速切掉,落在地面的時候眼睛仍舊張開,驚吓的表情也沒有改變,在有些情況之下割開肋骨帶來一個緻命的切口,使得受傷的人很快死亡。(狄奧多羅斯,曆史叢書,XVII,58)不過,善于為尊者諱的阿裡安則對上述戰況不置一詞,轉而着力描寫大相徑庭的馬其頓軍右翼戰況。早在戰車出擊前,大流士就貿然出動了塞種騎兵和巴克特裡亞騎兵,最終被馬其頓騎兵擊退。此時,缺乏騎兵配合的鐮刀戰車雖然企圖沖散馬其頓方陣,卻也遭到掩護騎兵的馬其頓輕步兵痛擊,一輪輪猛烈投射殺傷過後,戰車沖擊威力銳減,雖然有少數沖入方陣,也造成個别駭人創傷,終究是無濟于事。
▲龐貝城遺址馬賽克中的波斯騎兵形象
尾聲
盡管阿裡安在主要參考繼業者托勒密的《亞曆山大遠征記》中将鐮刀戰車寫得近乎廢物,但諸多繼業者卻表現得頗為誠實。公元前301年,在決定亞曆山大帝國瓜分命運的伊普蘇斯決戰中,取得最終勝利的塞琉古軍隊便出動了至少100輛鐮刀戰車。直至羅馬人一統地中海為止,鐮刀戰車都在帝國廢墟上的大小交戰中扮演過種種重要角色。其後,盡管鐮刀戰車不再成為實戰利器,卻始終沒有離開武器專家和設計師的頭腦,直至19世紀中後期,人們仍然可以找到腦洞大開的鐮刀戰車後繼者。總之一句話,套用一句網絡用語,形容古希臘人對于鐮刀戰車的态度,“嘴上說不要,身體還是誠實的。”
▲ 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塞琉古鐮刀戰車設想圖
▲約翰·考恩1855年的蒸汽朋克狂想,圓形自走鐮刀戰車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吳畋,任何媒體或者公衆号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将追究法律責任。部分圖檔來源網絡,如有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