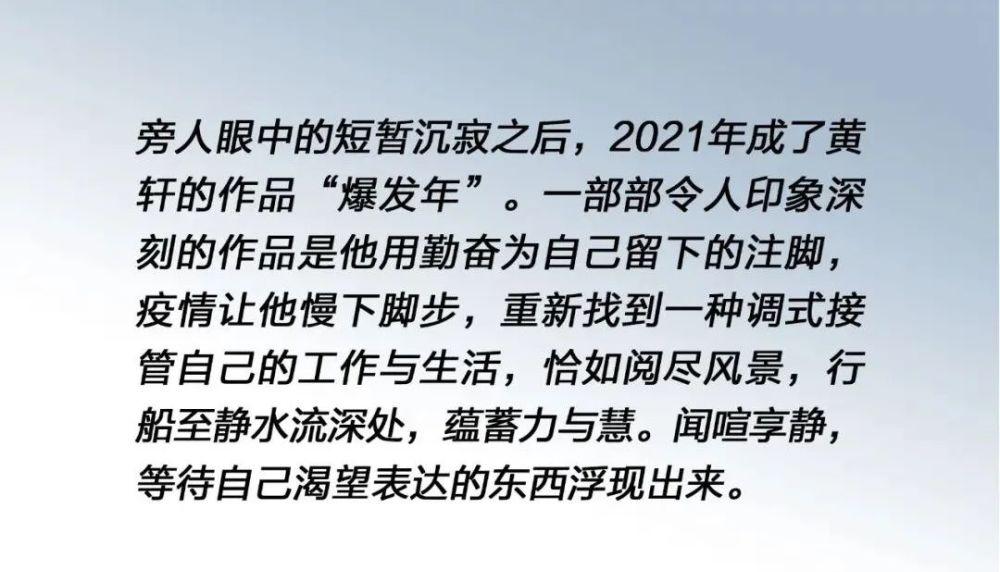
灰色“CD DIAMOND”提花羊毛針織開衫、白色
棉質高領打底衫、灰色羊毛運動長褲和銀色飾面
CD ICON和珠飾項鍊
均為Dior
我們在挑高式影棚内跺腳歎冷時,黃軒精神飽滿地出現,同我們打招呼。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内搭海魂衫,牛仔褲下是一雙袋鼠鞋,簡單随性。拍攝結束換衣服的間隙,假如你不經意對上他的視線,他會沖你颔首微笑,落落大方,這同他在聊天過程中平穩的語調、準确又有資訊的措辭、專注的眼神、幅度極小的面部表情一起混融構成了某種印象:黃軒是淡然而從容不迫的。
這種從容不迫背後的勤奮在2021年一一顯形:從年初的《山海情》,到年中的《1921》《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再到年末的《烏海》《風起洛陽》,幾部作品接力沒有斷檔,口碑良好,将2021年标注為黃軒的事業“大年”。
在黃軒的口中,曾經的他像“籠子裡跑起來的小白鼠,永無休止”,疫情發生之前,連續五年的大年三十,他都是在劇組度過的。“我媽到劇組來了,跟大家吃個年夜飯,第二天起來,早上我們倆喝口茶,聊聊天,我就開工了。”密集的工作節奏織進身體裡,習焉不察。
淺米色風衣 Gar on by Gar on
橘色毛衣 Isabel Marant
白色亞麻襯衫 Loro Piana
然而一切還是發生了改變。“如果以開車來說,疫情之前,我可能開的是時速120,疫情之後,我現在是時速80。”這一切都源于一次度假。原本黃軒隻想帶家人在山裡度過安靜的5天,誰知疫情将這時間抻長到了三個月。黃軒隻帶了幾件衣服,物流中斷,生活退化為最原初的樣貌。直到快遞恢複,黃軒買了一隻可以煮火鍋的鍋,幾本書,朋友為他寄來了筆墨紙硯,寫書法,看書,日子又開心充實了起來,黃軒乍然間頓悟:“其實我的生活元素不用太多,就這幾樣,心裡一下子踏實了不少,又重新規劃自己未來的節奏。”
《山海情》就是黃軒重整節奏後接的戲,一提起來,盡管話語克制,可其間仍是滿滿的興奮之意。“我一直很想拍一個西北的故事,演一個西北人,說西北方言,這是我對故鄉的一種情結,我也一直很想跟孔笙導演合作,當孔笙導演找我時,等于4個願望同時實作,我非常激動。”
願望達成,沒有過鄉村生活曆練的黃軒卻對自己能否演好馬得福這個扶貧幹部心懷疑慮。他和同組的其他演員提前進駐當地農村,定妝試妝,每天在戈壁灘上搭景排練,與世隔絕。彼時正值炎夏,烈日灼灼,開車至布景地花費時間頗長,四野之間舉目望去一棵樹也沒有,風起處,黃沙撲面,沒過多久,皮膚皲裂,嘴唇泛皮。也正是諸般艱苦,一下子就将黃軒帶入了《山海情》的氛圍之中。
恣意潇灑的古裝戲,光鮮時髦的當代都市戲,風雲變幻的民國戲……如今,黃軒的表演履曆裡又多了一出溫暖濃情的農村扶貧戲,很多人至今忘不了劇中的馬得福在聽張主任描繪吊莊的未來時眼中之光,和他在晨光中望見初戀情人水花時從嘴角漫溢到眼睛中的帶淚之笑,觀衆的喜愛與認可讓黃軒收獲了成就感。遇見一個好的角色、一個好的表演狀态,都令他心懷感恩。
緊接着,黃軒又在《1921》《長津湖》中貢獻了精彩的表演。兩個角色李達、毛岸英都是曆史上的真實人物,飾演這一類人物的難點在于如何進入角色,又不被真實性所綁架。對黃軒而言,書籍、傳記、僅有的一點圖檔和影像,都是揣摩角色的切入口,但更為切中肯綮的是一種了解方式:“他們究竟在幹着些什麼事,他們那個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在一個什麼樣的曆史環境下?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願望去做這些事情?”他們都是黃軒眼中年輕而又勇敢的理想主義者,再聯系國家遭受苦難時的影像資料或故事,共情自然而然就發生了,李達、毛岸英也借由黃軒在銀幕上再“活”一次。
棕色大衣和棕色印花襯衫 Amiri
棕色長褲 Isabel Marant
從業多年以來,除了少有的幾次滑坡,黃軒挑選角色的眼光一直為人稱道。
他心中自有對好角色的要求,或是要具有代表性,是一部分人群的縮影;或是特殊人群的一員,處于陰影帶而不被關注的人,比如《推拿》中的小馬;此外,這個角色需要容納很大的内心空間,有喜悅、恐懼、焦慮、憤怒種種複雜交織的情緒,正面臨自我與世界的碰撞與和解。無疑,《烏海》中的楊華正是這樣一個角色。
關于《烏海》的幕後故事,黃軒在不同場合分享過很多次,他是在一個非常感性的狀态下接下了這個角色。原本拍完《隻有芸知道》的他,因為《烏海》中楊華身上幾乎過載的情緒而想要拒絕這個劇本,卻因為和導演周子陽的一頓飯而改變了主意。
“我跟導演聊天,我知道他想表達的是怎麼樣一個狀态的人物,但是具體到劇本上,其實還是缺東西的,不是所謂的已經很成熟了,我覺得他給了很多的空間讓演員來再次創作。是以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刺激的創作體驗。”
拍攝《烏海》的經曆,用黃軒的話來說,是把“自己的很多東西掏出來用”的過程,是一個剔骨還肉般全身心浸入的過程。接下戲之後,甫臨現場,他就感到非常不安,意識到必須得硬着頭皮上,“很多場比較重要的戲,都得跟導演探讨很久,得梳理好自己的心理活動,梳理好自己的行為,梳理好自己的語言”。
深綠色羊毛西裝夾克、白色棉質高領打底衫、
白色棉質長褲和銀色飾面
Christian Dior Atelier吊墜項鍊均為Dior
為了貼合人物,黃軒主動拒絕了劇組最初為他安排的當地飯店一間陽光充沛、擺放了鮮花與水果的房間,住進了另一間陰冷的、沒有采光的房間。每天窗簾半拉,他日日穿着楊華的衣服,不洗頭,頭發打绺成結,用各種方式折磨自己,“我事後看電影,覺得自己面相都變了,整個人都是浮腫變形的”,那是一種和故事中的楊華一樣将自我逐漸逼至絕境的體驗,而風沙惡劣的戈壁灘就像是心理環境的某種外在顯化,“從生理上的難受,再逐漸進入到心理上的難受,然後再走進這個人物”。
我們好奇,如果與角色融合無間之後,是否放下角色會變得艱難,黃軒否定了我們的想法,演了十五年的戲,告别角色也變成了一件職業化的事。自然,還是需要一點儀式,殺青之後,安安靜靜地待在房間裡回味拍攝的點滴和人物的曆程,有時長歎一口氣,就此打住,随後洗澡,換上自己的衣服,噴一點香水,外出飽餐一頓,第二天坐飛機回京,回到家中,回到自己的生活狀态,“那些場景就像一場夢一樣過去了。當然它已經長在你的身體裡,以記憶或夢境的形式存在,就像我們回憶起小時候的一段往事,或者是去年的某一段經曆”。
時而也會有貪戀角色狀态、不舍得離開的時候,比如《妖貓傳》中深情、潇灑、又有點小癫狂的白居易,黃軒就會将那種狀态一直延續到生活裡,這或許是專屬演員的某種魔法和特權:将角色的一部分生命攜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藍白拼色羊毛夾克、白色棉質高領打底衫、
Christian Dior Atelier吊墜項鍊
敏感是一個演員與生俱來的天性,一次眼神交會,視線低回,笑意,擦肩,錯身,都能生出無限興味,這與一個人發達的感性經驗是分不開的,而感性經驗又往往是發散的、随機的、無迹可尋的、文學化的,當黃軒提起自己對于童年的記憶時,就有這樣的特質:“有時候你會記得一件特别不經意的事,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人,一個陌生人對你說過的一句話,或者對你做的一個行為,或者是一種氛圍,某一個樓的樣子,某一種光線,某一種氣味。”
生活中,黃軒是一個時時在感受的人,觀察和觀察所引起的細微的心靈反應,都會被他汲取為表演素材:“如果有一天我演一個記者,我采訪人的時候,我可能就想到,今天你采訪我的時候,你在很認真地聽我說話,你在接受我的資訊,然後你在記錄的時候,是不看字的這種細節。”
而這也意味着,他的腦中經常有另外一個意識在看着自己,觀察他的反應、行為、思想活動和情緒,這個意識也會持續攝取周圍環境裡的資訊,空氣、溫度、氣味,從一個人身上聯想衍化出不同的枝蔓,當意識保持活動時,它在黃軒周身構成了一個流通的能量場,亟待有一天能夠灌注到表演當中。對于這項特殊的禀賦,黃軒感到“又愛又恨”,“這是一個很珍貴的元素,有時候又覺得,哎呀,太累太煩了”。
白色亞麻西裝和白色亞麻襯衫
均為Loro Piana
當思緒交雜繁亂時,黃軒就會寫書法。在他眼中,文字不隻是一個符号,一個代碼,當它轉化為書法,從筆端流出,傳遞情感,正是對藝術的抵達,同時,他也将其視為一種靜心的方式。這個習慣從很早之前就開啟,中間中斷過幾年,但仍然保留了下來,“我喜歡毛筆尖摩擦在宣紙上的感覺,它把我的注意力,把我散亂的心一下子就縮在這個筆尖上,特别美妙”。
疫情改變了黃軒工作和生活的步調,《風起洛陽》拍攝結束之後,他休息了三個月,天氣好的日子裡,他爬山,逛公園,在大街小巷遊走,也同朋友小聚,工作、社交,一切去繁從簡,這同他對自己演員生涯的劃分暗合,從初始階段的好奇、摸索、了解、忐忑,到下個階段嘗試各種各樣的角色,如今,黃軒問自己更多的是:“借助演員這個身份,借助角色,你更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他正在拍一部叫作《歡迎光臨》的電視劇,在裡頭,飾演一個酒店門童,門童本身的職業屬性,作為小人物如何生活,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這些牢牢攫取了黃軒的興趣。輕喜劇的表演方式是他從前未曾嘗試過的,而帶了一絲荒誕味道的情節和台詞都對他構成了新的挑戰。
棕色大衣和棕色印花襯衫 均為Amiri
棕綠色拼接長褲 Isabel Marant
白色高幫靴 Dior
在挑戰面前,黃軒為他久久思考的問題找到了一個答案,也是他的表演之船行至靜水流深處抛下的一個錨點:“其實作在很多人都面臨很多焦慮、風險,是以我還是想傳遞一些溫暖的、喜悅的能量,這些可能不能實質地解決很多問題,但是起碼讓别人看到你的表演,看到你的作品,能心生出一些歡喜。”
攝影 姜南(AStudio)
采訪、撰文 倉鼠
造型 Sherry
時裝編輯 Steven
妝發 張帥
美術 壹鑫置景
服裝助理 小塔
編輯 fu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