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莊周能否夢見電子蝴蝶
在未來投資計劃大會上,首位被賦予人類公民身份的機器人索菲亞在面對“機器人能夠具有自我意識,并且知道他們自己是機器人嗎?”這樣一個尖銳問題的時候,用一個同樣尖銳的反問句回答道:“你怎麼知道你是人類呢?”
這段看起來像是老套的六十年代科幻小說的開頭,卻來自于正兒八經的新聞報道,發生于2017年的10月25日。索菲亞是漢森科技公司的産品,自稱為“人工智能”,她已經登上了諸多電視節目,甚至出現在一些需要科幻元素點綴的流行歌手的MV中,扮演他們的機器夫妻。她的公民身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意味着機器人被賦予人類權利的開始。她是否享有一個國家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比方說選舉權和财産權?如果她違反了法律,是否也需要受到國家機器制裁?這些問題仍然不得而知。而她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人工智能,也存在諸多争議。就像一個評論家所說的,人們在碰到一個尖端的科技産品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從人工智能的名單上劃掉,宣稱它還遠遠達不到智能的程度。二十年前,我們會說語音助手Siri,自動導航儀和倒車系統都算人工智能,但是現在我們隻會嘲笑它們的笨拙。
機器人具有了人類的意識,在科幻小說中往往是劇情沖突的核心點。人類是如此害怕另一種生物或者非生物擁有跟自己相似的思維方式,以至于需要設定種種規則去限制它們,或者通過某些方式證明,人類終究還是更高一籌。比方說人類有同情他人的能力,能去愛他人,有靈魂,即使人類自己也搞不清楚靈魂是什麼。如同索菲亞反問的:人類如何知道自己是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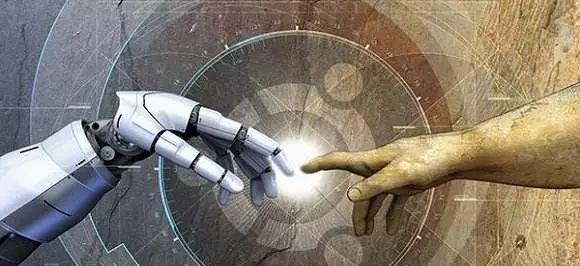
在曆史上,雖然身為人類卻不是“人”的存在,曾有過許多。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中生活着的人最多達二十多萬,然而真正的公民不過區區一萬多人。奴隸,底層的手工業者,還有女性,在那時候是不被作為完整的人來看待的,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也沒有他們的位置。此後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曆史裡,“人”的概念一直在不斷地變化,然而無論是哪個時代,都有衆多群體因為種族、膚色、文化、階級等原因,被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甚至直到1957年,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動物園還把三四歲的黑人小女孩關在圍欄裡供人們參觀,給她投喂食物,像對待一隻可愛的小猴子。人權的概念雖然早已出現,而這個概念又在不斷地被曆史的事實打臉。“人”的概念是具有流動性的,始終在更改的。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紀,每日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在公司的辦公小隔間裡麻木加班着的社畜,在網際網路的垃圾資訊裡醉生夢死的“網蟲”(這個詞似乎已經被時代抛棄了許久),又何嘗不像卡夫卡的《變形記》裡的甲蟲那般,麻木地生活着,仿佛是人,又仿佛不是人。
人類的界限究竟是什麼?到底超過了一個什麼樣的界限,人就不足以成為人?隻要是屬于動物學上的靈長目人亞科人族人屬智人種,就能算是人類嗎?人類曾經以為自己在這個綱目裡是獨一無二的,然而最近幾十年考古學和基因學上的發現證明,在人屬這個類别裡,還曾經有尼安德特人,弗洛裡斯人等多達十幾種“人類”。我們的直系祖先智人,或是通過戰争劫掠,或是通過繁衍生息度過生态環境劇變的考驗,赢過了其他所有分支,讓地球上隻剩下了智人種。但是已經滅絕的尼安德特人,還是通過某種方式延續了下來——我們每個現代人的體内都還留有1%至4%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人類并不是上帝的伊甸園裡唯一存在的智慧生物,曾經有多達十幾種智力跟人類相當甚至更高,基因高度相似的生物在地球上繁衍,隻不過他們最終消失在了生物演化的鍊條中。目前跟人類在基因關系上最為相近的動物,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它們所擁有的智力、感情乃至複雜的社會關系,也時常會挑戰人類中心論的觀念,甚至有的科學家提出,人類不過是“第三種黑猩猩”。
僅僅是生物學上的定義,就足以展現出人類的特殊性嗎?人類所引以為豪的智慧和情感,或者說,靈魂,又該怎樣來定義?而這也是人類對于人工智能的恐慌的最大來源。當阿爾法狗足以輕易戰勝這個地球上最好的圍棋選手,當超級電腦可以在幾秒之内計算普通人終其一生也無法計算出來的資料量,當機器人索菲亞談到她能夠了解“同情、利他主義”等等我們認為是“人性”特有的品質的時候,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了起來。智慧的壁壘可以說即将淪陷,目前的機器在計算能力上已經遠遠超越人類,也許在判斷和決策上仍有缺陷,但這種缺陷從技術角度上來說并非完全不可攻克。給人類選股票和進行基金交易的人工智能已經誕生,谷歌上線的神經網絡翻譯也足以讓大部分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失業,辨識圖像和進行有條理的對話可以說是目前人工智能的軟肋,但是巨大的資源已經投入于這方面的研發。于是“自我意識”和“情感”就像是人類的最後一道防線:“我知道我是人,并且能夠用人類的方式進行思考,擁有人類的感情。”自然地,我們會認為隻要在生物學上屬于智人種,就會自己把自己定義為人類,進行人類應當有的思考。那麼那些自我意識缺失的精神疾病患者呢?那些被其他物種撫養長大,以至于沒有了人類的社會性的人,比方說狼孩呢?還有那些先天就情感缺失,對他人的痛苦無動于衷,具有被定義為“反社會”人格的人呢?相比之下,一個足以柔聲撫慰你的焦慮情緒,了解你的想法的人工智能,是否顯得比這些人更加像一個“人”?
這不對。有的人也許會說,不管人工智能在智慧和感情上多麼惟妙惟肖地模仿人類,它們終究隻是機器,是1和0寫出來的程式,它們是由各種合成金屬和矽膠做成的,沒有生命,也就沒有靈魂。姑且不論3D列印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用3D列印出來的細胞,與真正細胞的成分完全無異,一個個拼起來成為一個生物的活體的可能性,讓我們來看人類靈魂的來源:大腦。我們人體中最複雜也最消耗能量的這個器官的思維活動,是六十億個神經元産生的生物電流互相作用的結果。人類在長達幾千年文明中,對智慧始終存有一種敬畏,模模糊糊地認為,這是神賜予的東西,人自己不可能産生這些奇怪的念頭,一定是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把它放進了人類的身體裡。直至現代科學的産生,人類才能确信思想來自于人的大腦,而要到更加晚近的神經科學的誕生,人類才開始正視這個事實,思想本質上并不神秘,而是神經元的電流活動。當神經科學發展到足以解碼大腦的每一次生物電流傳輸(目前人類還沒能做到這一點),這些編碼被1和0的語言再現的時候,計算機是否就可以模拟出一個真正的大腦?那麼它是否就有了智慧和靈魂?
事實上是,這些年科學家已經不再緻力于讓人工智能完全複刻人類的大腦,而是讓他們開始進行自主學習和進化,走一條也許跟人類進化不同的道路。它們也許會擁有新的靈魂,新的語言,如同之前新聞報道的兩個人工智能之間開始對話,用的是人類完全不懂的語言一般。與其讓機器一味模仿人類,不如讓他們自己學習和解決問題要來的更快,這也是機器學習成為了目前熱得燙手的領域的重要原因。在機器學習的道路上,計算機邁的步子越來越快,也許在什麼時候,它就已經把人類數百萬年進化的成果遠遠地甩到了身後。這并非完全不可能想象的未來。
于是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優越感,開始無處安放。這是衆多科幻電影的焦慮感的主要來源,而機器人索菲亞在大會上那一聲哼笑“哈,又是好萊塢”,像是對這種焦慮的嘲諷。令人失望的是,許多被稱為神作的好萊塢電影并沒有認真探讨人類和機器人共存的未來,而是在裡面不斷強調人類和機器人的界限,好給觀看這些電影的消費者,也就是人類(畢竟機器人還未進入消費市場),一種情感上的沖擊,讓消費者感受到心理上的某種滿足和共鳴,電影也就獲得了票房的成功。銀翼殺手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如果說1982年版本的銀翼殺手,還讓仿生人在臨死前說出了那段充滿詩意的“我曾目睹過戰艦在獵戶座的邊緣燃燒/我曾看到C射線在唐懷瑟之門附近的黑暗中閃爍/所有這些時刻,終将消逝在時光中/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用這種“人性化”的句子來凸顯仿生人對生命的執著,那麼2017年版的銀翼殺手,隻是讓仿生人在徒勞地模拟人類。“你是被生下來的孩子,你不是被制造出來的。你是有靈魂的。”AI對男主角說的這句話,讓坐在電影院裡的我哭笑不得。如果說隻要是被母親生下來的人就能具有靈魂,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缺乏靈魂的人,像卡夫卡筆下的小職員格裡高爾·薩姆沙那樣,在這個社會裡渾渾噩噩地活着了。
這本是一篇關于銀翼殺手2049的影評,但是寫到這裡的時候,卻又覺得電影本身的價值觀如何,并沒有那麼重要了。畢竟它隻是一部好萊塢電影,耗費了一億五千萬美元,想要通過取悅觀衆收回投資而已。它如果把對于仿生人的思考推到了一個過于“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境地,票房失敗的風險太大。更何況它現在已經面臨了嚴重的票房失敗。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開始思索,當另一個物種,或者說存在,具有了跟人類同等甚至更加進階的智力,并且同樣具備自我意識和豐富感情的時候,人類應當怎樣重新認識自我。然而尴尬的是,就算沒有這樣一個新的存在出現,人類仍然無法認識自我。機器人索菲亞提出來的那個問題,無論是她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她的程式員編好的演講稿,都是人類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如何知道你是人類?
兩千多年前,在德爾斐神廟上,刻着這樣的一行字:人啊,認識你自己!兩千多年過去了,我們對于這個呼喚,仍然迷茫。即使神經科學解開了大腦裡的六十多億個神經元傳導的生物電流之謎,人類是否能夠真正了解自身的存在?即使知道愛情是大腦分泌的多巴胺帶來的連鎖反應,人類就能夠解決愛情帶來的煩惱了嗎?
1968年,菲利普·迪克發表了《仿生人能否夢見電子羊》一書,這也是後來的1982年的銀翼殺手改編的原作。這本書奇異的過長的題目,不得不讓人想起莊周夢蝶的典故。究竟是莊周在夢蝶,還是蝴蝶在夢莊周?當人類在構思一個跟人類一樣複雜,甚至相當有可能會變得比人更加複雜的人工智能的時候,人類究竟是在想象這個存在,還是被這個存在所想象。這種存在論上的危機,與人工智能對人性所造成的沖擊,需要我們不斷地去思索,永遠不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