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子凡
來源:《曆史評論》2021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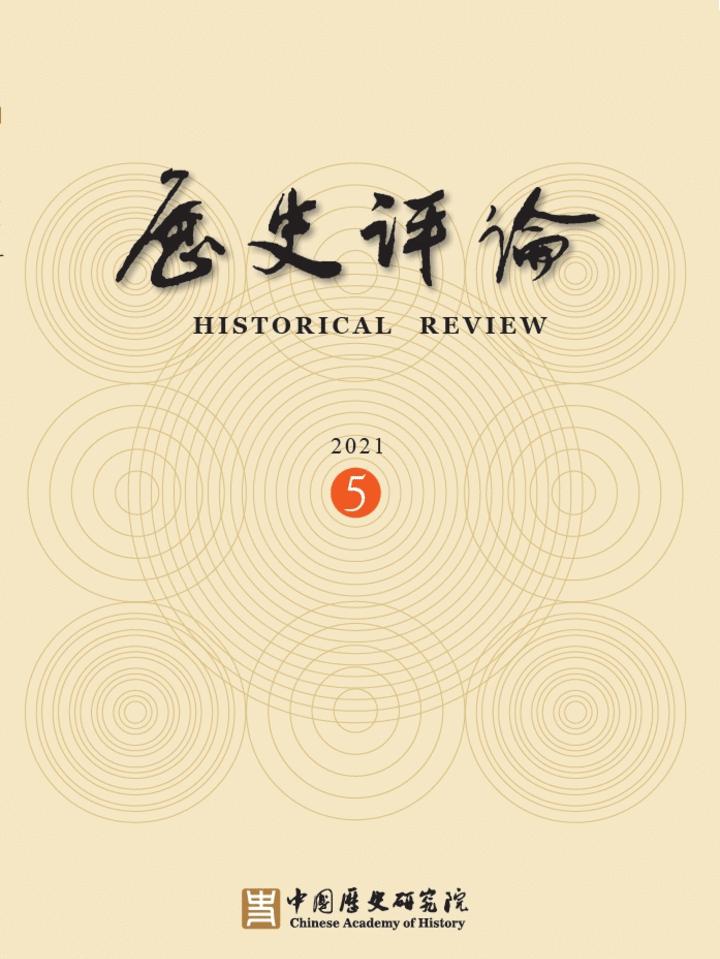
唐朝經營西域長約一個半世紀,憑借其強盛的國力在西域地區逐漸建立起較為堅實的統治。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人員往來異常活躍、中外經濟文化交往十分頻繁。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廣泛傳播,使得當地群眾對中原王朝的政治認同能夠長期維持,為當地的中華文化認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礎。
西域地區是連接配接歐亞大陸兩端的重要陸上通道,也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往的橋梁。由于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曆代中原王朝在國力能及之時,多緻力于經營西域,然而因其特殊的地緣狀況與複雜多樣的族群文化,要維持和平穩定的統治并非易事。唐朝對西域的經營,從不同層面着手,更着意于強化政治和文化認同,在一段時期内取得了很大成功。
循序漸進 因時制宜
唐代在西域的經營經曆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根據統治方式的不同,可以大緻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以西州都督府及安西都護府管轄為主的時期(630—692)。隋末唐初,西域地區主要是在突厥、鐵勒等北亞草原遊牧部族的控制之下。唐朝在貞觀初年開始逐漸介入西域,并于貞觀四年(630)在伊吾設州。至貞觀十四年滅高昌國,唐代已在天山東部地區建立了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市附近)、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遺址)、庭州(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三個正州,同時在西州設立安西都護府以統轄三州軍政事務。高宗顯慶三年(658)擊敗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後,唐代在天山以南的綠洲地區設立龜茲、焉耆、于阗、疏勒四鎮,同時将安西都護府移治龜茲以統攝之。此外,唐代還在西突厥諸部以及蔥嶺以西的粟特、吐火羅地區廣設羁縻府州,其名義上的羁縻地域一度遠至波斯邊境。這一時期,伊、西、庭三州主要以西州都督府為核心,四鎮則主要由安西都護府統轄。唐代在軍事方面主要采取都護府、都督府統領周邊鎮戍的防禦體系,日常隻是以較少的兵力完成防戍任務,遇到較大戰事則自中原組織大規模行軍與敵作戰。
二是軍鎮化與節度使統治時期(692—755)。自唐高宗龍朔二年(662)起,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開始進入西域,唐朝與吐蕃在四鎮地區進行了反複争奪。直到長壽元年(692),唐朝才逐漸穩固了對西域的控制,改變了四鎮在安西都護府統領下兵力有限的局面,将之逐漸更新為有3萬重兵駐守的鎮守軍。長安二年(702)唐朝又将庭州更新為北庭都護府,同時設立瀚海軍,天山東部的三州也有了大規模駐軍。唐代對西域的統治逐漸邁入軍鎮化時代。
玄宗開元初年,唐朝又先後設立安西節度使與北庭節度使。其中安西節度使統領天山以南的龜茲、焉耆、于阗、疏勒等處的鎮守軍,撫甯西域諸國;北庭節度使則統領設于伊、西、庭三州的伊吾軍、天山軍、瀚海軍,負責防制突厥、突騎施、堅昆等遊牧諸部。這樣就構成了以節度使統領軍鎮的軍事體系,軍事力量大大增強。同時,安西、北庭節度使又分别兼任安西、北庭都護,節度使成為唐代在西域實際的軍政首領。在強大國力的支撐下,安西、北庭兵力雲集,唐代對西域的經營臻于極盛。
三是安史之亂後的地方化統治時期(755—約792)。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玄宗緊急征調西北邊軍入關勤王,安西、北庭亦抽調大量精銳兵力分兩批進入中原作戰。吐蕃趁機出兵蠶食唐朝的西北州縣,廣德二年(764)涼州陷于吐蕃之手後,安西、北庭與中原的聯系斷絕,成為一塊飛地。此後唐朝隻能借道回纥,與留守西域的唐軍保持數年一度的通訊往來。這一時期,安西、北庭由于缺乏中央在财政和兵員等方面的支援,鎮守軍隻能采取自鑄銅錢、差科當地百姓等方式籌措軍費。至德宗貞元時期,安西、北庭相繼陷落,西域地區成為回鹘(回纥後改名回鹘)與吐蕃角逐的舞台。
中原制度與地方特色結合
唐朝對西域的管轄經曆了從都護府統領鎮戍到節度使統領鎮守軍的變化,但基本的行政制度一直是正州結合羁縻府州的統治模式。這一統治方式的實施,來源于唐朝對西域地區複雜的政治傳統與地方文化的了解,始終堅持中原制度與地方特色相結合,進而在一段時期内保證了唐朝在西域地區治理的穩定性。
考古證據表明,在青銅時代,西域地區就是不同族群往來遷徙及落腳之處,進而造就了該地區在族群與文化上的多樣性。唐朝經營之初,西域地區即可以劃分出多個特色鮮明的政治文化區域。扼守絲路孔道的高昌國,其主體居民是十六國時期遷徙至此的漢人,史載其立國百餘年間“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一直傳習《毛詩》《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大量的出土文獻也證明其在語言、制度、習俗等各個方面保持了漢文化傳統。天山以南的龜茲、焉耆、于阗、疏勒等綠洲國家,雖然也采取以農耕為主的生産方式,但因其為東西文明交彙之地,是以文化面貌與高昌迥然不同。綿延數百公裡的天山山脈腹地及其以北的草原地區,則是西突厥十姓部落、葛邏祿、處月、處密等遊牧部族活動的地域。此外,在東部的伊吾、鄯善等地又有由粟特商人建立的城堡聚落。西域地區的政治形态與文化面貌可謂複雜多樣。
由于絲綢之路日趨繁榮,大量商賈東西往來不絕,唐朝對于西域的認識也遠超前代。唐朝的天下觀念中自然也融入了相容中原與四夷的因素,如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唐朝在西域采取了因俗而治的統治模式。
首先是在原高昌國及其周邊設立正式州縣,行用中原制度。唐平定高昌國後,直接以高昌之地為西州,以其故都高昌城為州府治所,以原高昌國之四郡為西州之四縣,原高昌國的屬縣也被重新編為鄉裡。這樣,高昌國的國—郡—縣體制就直接轉化為唐朝的州—縣—鄉裡。根據出土文獻記載,唐朝确實在西州實行了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中原制度。可見,唐朝很好地利用了高昌國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漢文化傳統,平穩地實作了制度的推行。西州建立之後,成為唐朝經營西域的前沿基地,除了利用其地緣優勢之外,西州的漢人官吏與百姓也為唐朝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成為西州乃至庭州、安西四鎮進行行政管理與鎮戍防禦的重要力量。唐朝以西州為核心,連同其附近的庭州、伊州,控制住了中原進出西域的門戶。
其次是在天山以南的綠洲地區建立羁縻府州與軍鎮結合的統治方式。至遲在高宗顯慶三年擊敗西突厥後,唐朝就在天山以南的龜茲、焉耆、于阗、疏勒四地設立羁縻都督府以進行管理。羁縻府州不同于正州,其都督、刺史雖然名義上由朝廷任命,但大多由當地首領世襲擔任,當地的民政事務也大多是由首領負責,不必完全行用唐的律令制度。唐朝在綠洲地區設立羁縻府州,而不是像高昌那樣直接建立正州,無疑是考慮到綠洲地區并沒有類似高昌的漢文化傳統,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其固有的體制,隻是将其納入羁縻府州的架構中。另一方面,由于綠洲地區具有農耕文明的定居特點,且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唐朝在設立羁縻府州之外,又在諸國設立鎮戍。長壽元年以後,四鎮逐漸更新為鎮守軍,又有了大量來自中原的兵士在此駐守。這樣就在綠洲諸國形成了既有當地都督刺史管理民政,又有節度使、鎮守使管理漢軍兵馬的統治方式,張廣達稱之為“胡漢結合的軍政體制”。
最後是在西突厥、葛邏祿、處月等遊牧諸部設立羁縻府州進行統治。針對這些遊牧部族往來遷徙,不易分兵鎮守的特點,唐朝僅是羁縻以治,除了任命其首領為都督、刺史外,僅派遣個别漢人官吏擔任參軍,幫助其撰寫表疏。而這些羁縻府州又分别隸屬于安西都護府與北庭都護府,這是一種看似松散卻又有一定集中的管轄方式。
這樣,唐朝就在西域地區建立起正州、羁縻府州與軍鎮結合、羁縻府州三種統治方式,它們分别對應于具有漢文化傳統的高昌、天山以南的綠洲地區、天山腹地及其北麓的遊牧部落,這是一種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多樣化統治模式。這保證了唐朝既可以通過正州和駐軍作為統治根基,以羁縻府州為緩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顧綠洲地區及草原諸部的政治文化傳統,實作平穩統治。
中原文化産生深遠影響
自漢代張骞鑿空西域,中原王朝便開啟了經營西域的曆程。在此基礎上,唐朝對西域的經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原文明也更加廣泛地進入西域,并與其他文明互相激蕩,對西域曆史走向産生了重要影響。
一是将郡縣制推廣到西域地區。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區設郡立縣有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漢代僅是設立西域都護、西域長史以統管西域,十六國時始設高昌郡,隋代又曾設有伊吾郡。唐朝前進了一大步,除了在高昌設立西州、在伊吾設立伊州之外,還在天山北麓設立庭州,不僅設立州縣的範圍超過前代,而且實作了長時間的有效統治。這樣,由中原王朝直接統轄且完全行用中原制度的範圍,已經向西跨越了陽關、玉門關,達到了天山東部地區。與此相對應,唐代官方所稱“西域”的範圍也發生了西移。唐初“西域”仍是指敦煌以西,伊、西、庭三州設立後則是指三州以西,而控制四鎮之後便隻将蔥嶺以西稱為“西域”。州縣的擴張與“西域”的收縮,反映了唐朝在西域統治的不斷深入,最終形成了漢唐時期西域經營的最遠邊界。
二是西域對唐朝的政治認同大大加強。唐朝憑借其強大的政治和文化實力,逐漸在西域地區建立起政治認同。例如,從吐魯番出土墓志看,進入唐朝後當地墓志開始改變高昌地區傳統的書寫方式,轉而逐漸與中原趨同,開始出現“大唐啟運,澤被西州”等措辭,展現出對新邦大唐的認同。又據《舊唐書》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叛時,于阗王尉遲勝“自率兵五千赴難”,說明随着唐朝在西域經營的深入,安西四鎮也建立起對唐朝的政治認同。唐朝的影響力甚至遠及蔥嶺以西,玄宗時拔汗那國一直與唐朝關系密切,玄宗冊封其國王為奉化王,改其國名為甯遠國,并遣和義公主與奉化王和親,安史之亂爆發後,拔汗那國也曾派兵入援。
三是中原文化在西域廣泛傳播。西域地區曆來是多種文化交流彙聚的場所,随着唐朝經營西域的深入,中原文化也不斷西傳,在西域産生了深刻影響。《舊唐書》載唐代名将哥舒翰父為突厥人、母為于阗人,生長于安西四鎮的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可見當地人普遍學習漢文化的情形。在和田出土的唐代文書中也見有《蘭亭序》的臨本,作為中原文化中最經典的書法範本,《蘭亭序》的發現印證了中原書法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廣泛傳播。唐朝也在西域地區建立了屬于漢地佛教系統的官寺,于阗、疏勒、碎葉等四鎮地區都有漢僧主持的官寺,與行用小乘佛法的當地寺院并行不悖。粟特地區此前主要行用按希臘、波斯樣式打制的無孔錢币,7 世紀中葉以後,該地區開始出現仿照唐朝錢币鑄造的方孔銅錢,展現了中原文化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影響。
唐朝在西域近一個半世紀的經營,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繁榮,加深了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融。圖為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官俑,其穿着打扮和中原地區的官吏并無差別。引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絲路瑰寶:新疆館藏文物精品圖錄》,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
四是唐朝在西域留下了豐厚遺産。唐朝的統治在西域産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即使在安史之亂後唐朝逐漸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也依然在延續。五代宋初時于阗王李聖天雖然與唐朝皇室并無血緣關系,卻“自稱唐之宗屬”并冒姓李氏。而在李聖天之後的于阗國也保持了使用年号的做法。繼唐朝之後統治天山東部地區的西州回鹘政權,更是直接沿用唐朝在天山北麓等地建立的軍鎮和戍堡,并将其發展為經濟貿易中心,延續了絲綢之路的繁榮。《長春真人西遊記》載,丘處機在西行途中,曾在鼈思馬大城向當地的僧、道、儒問風俗,其人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可見直到成吉思汗時代,北庭故地依然生活着浸染中原文化的儒、道之人,也依然留存着碑刻、佛藏等唐代文化遺存,唐朝的西域經營也成為當地人的曆史記憶。
自唐太宗貞觀年間至唐德宗貞元年間,唐朝經營西域長約一個半世紀,憑借其強盛的國力在西域地區逐漸建立起較為堅實的統治。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人員往來異常活躍、中外經濟文化交往十分頻繁。雖然唐朝因安史之亂的爆發而國力大減,最終放棄了對西域的經營,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廣泛傳播,使得當地群眾對中原王朝的政治認同能夠長期維持,為當地的中華文化認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礎。
作者機關: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