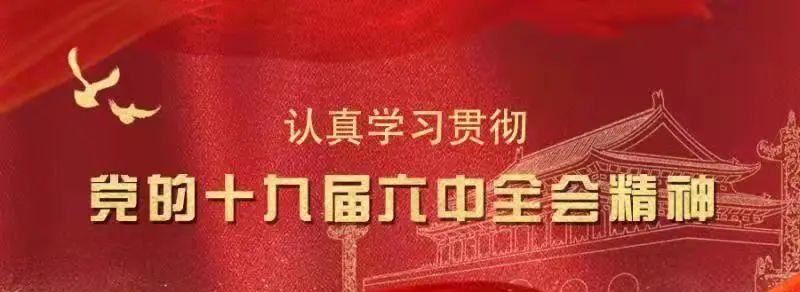
【千問千尋大運河】一代大俠霍元甲和他的精武故鄉
一座城市形成的緣起,往往源于河流帶來的人口聚居;一方人民的文化志趣,也常與水文環境緊密相連。地處“九河下梢”的天津衛,市民文化從誕生起就與滔滔河水密不可分。
天津市西青區被南運河橫穿而過,西青區精武鎮這片土地,湧現出霍元甲這位愛國英雄,也孕育了流傳百餘年不衰的精武文化。
位于小南河村的霍元甲像和霍元甲紀念館
“九河下梢”,霍元甲國術救國的思想搖籃
“萬裡長城永不倒,千裡黃河水滔滔,江山秀麗,疊彩峰嶺,問我國家哪像染病……”
這是電視劇《大俠霍元甲》主題曲中的幾句脍炙人口的歌詞。1984年春天,随着這部影視作品在大陸掀起萬人空巷的收視熱潮,“霍元甲”三個字響遍祖國大江南北,這位著名愛國國術家的家鄉——天津市西青區精武鎮小南河村,也逐漸為人所知。
與兩岸三地影視作品帶動的“霍元甲”熱不同,上世紀80年代以前,在霍元甲的故鄉精武鎮,他的名字早已在鄉間廣泛流傳。
研究霍元甲多年的文化學者王洪海回憶道,上世紀70年代初,他在小南河村的田間務農時,就常聽長輩聊起霍元甲的事迹。遠近幾個村的口口相傳中,那位名叫霍元甲的愛國國術家,成了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
改革開放後,王洪海開始萌生将人們閑談中的霍元甲轶事整理成文字的念頭,并陸續在報紙上發表短篇文章。随着上世紀80年代以來霍元甲及其弟子相關的文學、影視作品的傳播,霍元甲這個名字也與“一代大俠”的稱号相連接配接,為人所敬仰。王洪海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當年的盛況,并回憶起一段趣事。
王洪海手持自己多年來撰寫的霍元甲相關書籍
“1984年春天,由黃元申、米雪等主演的中國香港電視劇《大俠霍元甲》被引進到内地。當時我已在報紙上發表過一些霍元甲轶事的文章,正在醞釀一部關于霍元甲的長篇小說。不過我當時沒什麼‘流量思維’,看到這部電視劇火爆後,還擔心過會不會沒人願意耐下心讀我這部作品了。後來,時任江蘇人民出版社社長得知此事,來到我家鼓勵我盡快把小說寫出來。”
後來,王洪海以筆名“晨曲”創作的小說《霍元甲》于1984年7月付梓出版,首次印刷便印了70多萬冊,“霍元甲”三個字的火熱,可見一斑。
如今提及霍元甲,人們常會想到他“國術救國”“強國強種”的思想。王洪海多年研究認為,霍元甲這些思想的形成,與他一生在天津的經曆見聞密切相關。可以說,沒有天津這座城市,沒有天津在中國近代曆史的獨特地位,就沒有霍元甲這位愛國國術家。
天津古稱天津衛,自古因漕運而興,由海河幹流和五大支流組成海河水系與京杭大運河交彙于此,促進了這座城市近代工商業的繁榮,也滋養了運河文化。将運河文化深深根植于市民文化中,是天津的特色,也是霍元甲當年每日感受到的東西。
霍元甲30多歲時的照片
“霍元甲20多歲時,從小南河村老家來到當時的天津城區,在北門外竹竿巷(現在的大胡同附近)幫助好友農勁荪經營懷慶藥棧。這裡靠近三岔河口,南來北往的客商極多。懷慶藥棧進、出藥材貨物,都經南運河往返南方。”王洪海介紹道。
在這樣的環境中,霍元甲的愛國、強國思想逐漸被激發。近代的天津是較早向西方開放的城市之一,曾先後出現多個租界區,在這些近似“國中之國”的租界内外,外國人與中國人的沖突不時顯現,還曾出現過“天津教案”這樣的中國近代史上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沖突事件。
王洪海研究認為,出生于1868年的霍元甲,人生的前40年幾乎都在天津,他曾親眼目睹過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等曆史事件,将中國百姓受近代西方列強欺壓的屈辱曆史看在眼中。這些場景對霍元甲形成“強國強種,國術救國”,決心洗雪“東亞病夫”恥辱稱号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響。
“近代天津報業發達,霍元甲一方面親自感覺,一方面從報紙上獲知種種社會現象,列強的欺辱行徑、許多老百姓渾渾噩噩度日的樣子都在他眼前。比如霍元甲協助農勁荪經營的懷慶藥棧,它所處的那片區域,就曾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遭遇炮彈落下。”王洪海介紹道,霍元甲後來果斷應邀前往上海和英國大力士打擂、提出國術界不應囿于門派觀念、形成“以武救國”思想,這一切都與他曾身處天津這個大城市息息相關。
《申報》對霍元甲與大力士打擂的報道
霍元甲所處的時代,恰是中國近代一段屈辱的曆史,在這個背景下,霍元甲提出的救國、尚武思想難能可貴,也是以引起了人民群衆極大的共鳴,在他逝世後的一個多世紀裡,仍然不斷有文藝作品問世,經久不衰。
霍元甲玄孫女:對“霍元甲後人”之名曾有抵觸
深入了解後卻肅然起敬
如果說老百姓印象中的霍元甲,是曆史人物和藝術形象互相交織後的剪影,寄托着中國人民内心的民族自豪感。那麼對霍氏的直系後人來說,霍元甲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義,則更加浸潤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傳承”二字,對他們有着更深刻的意味。
天津體育學院國術教師霍靜虹是霍元甲的玄孫女,作為“霍元甲後人”,她對霍元甲有着特殊的情感。
霍靜虹
與很多人眼中“霍元甲後人”光環帶來的崇拜不同,霍靜虹小時候并不知道自己是霍元甲的後人,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并不願意被提及“霍元甲後人”的身份。
“我5歲半時,父母為了讓從小體弱的哥哥能習武強身,送他去參加國術班,我聽到消息後,要求一起參加國術訓練。當時,《大俠霍元甲》電視劇還沒有播出,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是霍元甲的後人。沒想到,哥哥最終沒有走練武這條路,我對國術反而有一股天然的喜愛,堅持了下來。”霍靜虹回憶道。
後來,霍靜虹來到體校念書,又考入北京體育大學國術系套路專業,畢業後先後在天津商業大學、天津體育學院擔任教師,如今在天津體育學院講授着太極拳、太極扇、傳統體育養生、傳統器械、太極推手等國術專業課程。2017年第13屆全運會群衆比賽中,霍靜虹還代表天津隊榮獲健身氣功團體賽冠軍。
霍靜虹走上習武之路與霍元甲并沒有關系,但“霍元甲後人”身份卻給少年時的她平添了不少壓力,“從小到大的國術表演有時會安排演講環節,我與霍元甲的這層關系,讓我經常被選中發言。可我擅長國術訓練,卻不擅長寫稿子、做發言,一到要寫稿子就怵頭。這讓我在學生時代和工作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願意被别人提及‘霍元甲後人’的身份。”
2017年第13屆全運會群衆比賽中,霍靜虹(右一)代表天津隊榮獲健身氣功團體賽冠軍
回憶這段經曆時,霍靜虹有些無奈。不過她也表示,曾經的抵觸情緒在近幾年中減弱了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對霍元甲生平的深入了解。
“2015年,我成為霍氏練手拳的代表性傳承人,專程到上海精武會、上海檔案館,通過曆史資料,了解我的高祖霍元甲的事迹以及精武會的經曆。這次調研,讓我對高祖的行為和經曆肅然起敬,作為他的後世子孫,應該學習他的責任和擔當,後世子孫也應該學習他為國、為民勇敢向前的精神。”
作為天津市非物質文化遺産霍氏練手拳的代表性傳承人,霍靜虹得益于多年習武的國術功底和從事國術相關職業的優勢,熟練掌握了全套共72個動作的霍氏練手拳,“霍氏練手拳是我霍家迷蹤藝諸多拳術中的一個入門拳術,非常基礎,和全民健康的理念不謀而合。如今,我一邊在家族中傳承這項拳術,一方面在教育崗位上傳授霍氏練手拳,還在天津市人民體育館體操國術隊、天津龍之風采教育教育訓練學校開展霍氏練手拳的習練活動。”
多年後再回頭看“霍元甲後人”這個身份,霍靜虹顯得自如、淡然了很多,“時至今日,‘霍元甲後人’成了我的一個标簽,它給我帶來宣傳、推廣、傳承國術的機會。每當學生知道我是霍元甲的後人後,都非常興奮、驕傲,學習起來也會更有動力。”
霍元甲文武學校:精武精神 傳承百年
如今提及霍元甲學武的故事,多少帶了傳奇色彩。曾有少年霍元甲因體弱被父親禁止學武,卻最終暗地裡練就一身出衆功夫的故事。這樣的細節是否完全符合曆史真實,可能已不太可考。不過研究者認為,霍元甲一家的習武家風,與近代精武鎮本身的尚武風氣有着重要聯系。
“霍元甲少年時,家鄉以習練國術聞名的不止小南河村,周邊不少村子都有練武風氣。一方面,這有身逢亂世的人們需要武技傍身的無奈;另一方面,不少人習武後去保镖護院,靠一身本領吃飯。比如霍元甲的父親霍恩第,就以保镖為業。”
霍元甲文武學校
1910年,霍元甲在上海逝世,但百餘年後,他的家鄉在傳承尚武風氣上未曾斷絕。在霍元甲故居不遠處,坐落着一處以國術為特色的民辦學校——霍元甲文武學校,這正是當地尚武遺風的寫照。在遠近不少市民看來,這所學校是當下傳承霍元甲愛國、尚武精神的一處瑰寶。
霍元甲文武學校校長郎榮标回憶道,1999年9月,他在霍元甲的故鄉創辦了霍元甲文武學校, 至今已經20多年了。談及在此建校的緣由,郎榮标直言和自己青年時期對霍元甲的崇拜有很大關聯。
郎榮标曾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手
“我是天津人,1984年進入天津國術隊,是天津國術隊第一批運動員之一。我和我夫妻侯冬媚都是國術運動員出身,很崇拜霍元甲這位愛國國術家。是以退役後,我們決定在霍元甲的故鄉開辦一所學校。學校現在以文化學習為主,國術訓練為特色。每年清明節,我們會組織師生進行對霍元甲的祭掃活動,日常教學也常教育孩子們傳承好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的精神。”
建校20多年以來,霍元甲文武學校已覆寫從幼稚園到職業高中,成為精武鎮乃至整個西青區的一張名片,不僅培養了衆多習練國術的青年才俊,還經常有師生赴海外參加國術比賽、表演傳統國術,弘揚中華文化。
霍元甲文武學校的國術訓練
曾在2017年點燃天津全運會開幕式主火炬的“津娃”潘天順就是霍元甲文武學校的一名學生。如今潘天順已經15歲了,正在就讀高一,平日仍在習練國術,尤擅一種中國傳統國術拳法——南拳。
潘天順在第13屆全運會上點燃主火炬
潘天順近照
在教書育人的同時,郎榮标還擔任了天津精武體育會會長。郎榮标介紹道,近年來,天津精武體育會按照建會章程和精武鎮弘揚精武文化宗旨,承擔着校外“國術六進”(即“進學校、進社群、進鄉鎮、進企業、進機關、進軍營”)工作的教育訓練拓展任務,策劃大型賽事以及與海内外精武會、國術團體聯誼交流等項工作。
談起霍元甲成立的精武會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郎榮标很有感觸。“國内外的精武會是非常多的,有些海外的精武會成了凝聚當地華人的重要組織,有些則開辦武館,将中華國術傳播到世界各地。這早已超出了單純的習武、練武範疇,形成了一種文化傳承,非常難得。”郎榮标感慨道。
也是在精武會的交流活動中,郎榮标感受到了身上肩負的重任,“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一次随隊赴馬來西亞參加文化交流活動時發現,當地華人團體組建的精武會很是興旺,但很多華人卻誤認為霍元甲是上海人,甚至誤認為是佛山人,反而很少有人提及霍元甲絕大部分人生都是在故鄉天津度過。而且很多人沒見過正宗的傳統國術,對我們的國術表演贊不絕口。我對此很是觸動,也是以希望能加強宣傳,讓更多人知道霍元甲與天津、與精武鎮的深厚淵源,讓中華國術發揚光大。”
國内外的衆多精武會
金庸先生曾在小說裡寫道,“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今天,很多人在霍元甲的名字後習慣加上“大俠”二字,其實正與這八個字同源同理。
郎榮标認為,“精武文化”之是以長盛不衰,正與霍元甲本人及其後人、弟子倡導以武救國,呼籲強國強種、決不當“東亞病夫”的精神高度有關,“霍元甲本人曾倡導摒棄門戶之見,要強身健體,協力救國。精武會的作用也從不是争一招一式、門派高下,而是着眼于愛國、強國,這種态度彌足珍貴。”
正如《萬裡長城永不倒》那首歌提到的,“沖開血路,揮手上吧,要緻力國家中興;豈讓國土再遭踐踏,個個負起使命”。霍元甲已逝世百餘年,但他短暫一生中的立身行事,卻都顯露着愛國救亡的光芒。也許,這就是這位愛國國術家至今仍受到海内外華人尊崇的最大原因。(津雲新聞記者 侯沐偉)
【千問千尋大運河】古宅、胡同、美食、文化……時空寶藏楊柳青!
天津市西青區楊柳青鎮的老鎮區。
古老的街巷,看起來有些破敗的老宅,卻是馮立最喜歡駐足的地方,站在老街中,歲月似乎靜止,老宅的每一片磚瓦都在安靜地訴說着百年經曆的風雨飄搖。
馮立
“70後”馮立是道地的楊柳青人,從幼時起,他就住在古老的窄巷中,看着楊柳青的楊柳依依、灰牆古道一天天長大。成年後,馮立沉浸在對楊柳青曆史的研究中,成為一名地方史專家。
因運河而興的楊柳青就像一個時空寶藏,沉澱和記錄着幾百年的曆史變遷,傳承和保護着中華的文化瑰寶。
被歲月洗禮的古宅遺迹中“藏”着楊柳青的過往,曆史被一點點揭開,百年前的楊柳青穿越時空,在史料記載和遺迹發掘中揭開面紗……
90多座清末民初老宅
戲樓、牌坊、仿清建築群……如今的楊柳青古鎮将傳統與現代融為一體,又充滿着濃郁的現代氣息。
運河一側,一片粉刷一新的白色圍牆内卻是另一番景象——清末民初時代的一座座宅院和民房保持着舊時的模樣,綠色圍擋将他們保護起來。老房子上精美的雕刻記錄着歲月的痕迹,曆經了百年風雨。
老鎮區的民宅被保護起來
馮立喜歡穿梭在這些舊時的古老街巷中,他一座座數過,目前,楊柳青西部老鎮區保留清末民初的建築仍有90多座,這些老宅中“藏”着楊柳青的曆史。
老宅上精美的雕刻
1992年,楊柳青蓆市大街遺址被發現,面積約1000平方米。據《西青區志》等資料記載,考古發現了包括金、元、明三個不同曆史階段的陶器、瓷器殘片和墓磚、度量衡用具。
蓆市大街遺址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史料記載,證明了楊柳青自金代就是大運河上的重要節點。
楊柳青鎮的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金貞祐二年,當城、沙窩、小南河寨等遺址的發掘證明楊柳青在宋代駐紮軍寨,此後形成人口聚集的部落。
楊柳青運河老照片
明清時,随着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楊柳青成為連接配接南北的重要漕運碼頭,楊柳青進入繁盛階段,彼時的楊柳青十裡長堤,楊柳依依,商賈如雲,景色秀美,一派江南水鄉的景象。
“楊柳青因運河繁榮,建築也順河而建,楊柳青幾乎沒有正南正北的房屋,所有的房屋都垂直于運河。”馮立說,運河南邊多為農田,北邊是商業和民宅,房屋沿着運河蜿蜒曲折,臨河的一面是門,友善接收船隻運來的貨物,船戶、農民、商人和楊柳青年畫經營者是當時楊柳青的主要人群分類。
清末民初的老宅
楊柳青街道突出的特點是以功能分區,靠近運河的是河沿大街,再之後有估衣街、豬市大街、蓆市大街、菜市大街等,民居分布聚集在各條胡同中。
街道的名字直接透露出每條街道的功能——估衣街賣衣服、菜市大街賣菜、豬市大街賣肉、蓆市大街賣葦席和筐籃等。每到春節,蓆市大街成為年畫市場……
豬市大街
如今的蓆市大街
菜市大街
馮立的記憶中還有楊柳青昔日的景象,小時候的他住在老宅中,走出院門,穿梭在胡同間,運河邊的楊柳依依,街巷中的大槐樹,古建築泛舊的灰牆……
對比清道光年間的《津門保甲圖》,楊柳青的格局從清朝至20世紀90年代基本未曾改變。
20世紀90年代末前的楊柳青
随着城鎮發展,楊柳青古鎮進行改造,但部分老宅被保護下來,老宅的古老和現代化的建築融合成多元化的楊柳青。
“仿版”南方建築
漕運帶來了楊柳青經濟的繁盛,也使楊柳青成為南北物資、文化的交彙地,很多南方獨有的建築藝術被複制到楊柳青。
如今被保護下來的老宅中,依然能看到獨特的建築風格,八字門、拐彎抹角、特殊的瓦檐結構、精美的磚雕,斑駁的百年石闆路……
楊柳青有一些建築風格,北方非常少見,而南方卻非常多。在幾年前的“尋根大運河”活動中,馮立和一行學者對運河進行了系統調研,在南方城市找到了這些建築的根源。
門邊的磚牆呈八字狀臨街,既滿足了自家院門有台階的需要,又不會影響行人從自家門前通過,“這種院門的樣式在天津其他地方都沒有,在常州、上海等地可以見到。”追根溯源中,馮立在南方找到了八字門。
楊柳青的八字門
石庫門是南方特有的建築形式,它起源于太平天國時期,江浙一帶的富紳為安全起見,修建住宅時把門戶改小,以求門戶嚴謹,楊柳青的民宅中也發現了“仿石庫門”的形式。
院牆臨街的拐角處出現一處抹角,為了便于行人、車輛同行友善,這是房屋主人公德意識的展現,也是一種建築與道德相結合的智慧。這種名為“拐彎抹角”的建築風格在北京比較常見,被視為皇城文化的展現。北京胡同的“拐彎抹角”如今已經基本消失,但在楊柳青被儲存至今……
楊柳青的“拐彎抹角”
為什麼楊柳青有那麼多華北罕見的建築形式?馮立認為,楊柳青是運河重要碼頭,而大運河連接配接着諸多江南城市,這些建築形式從大運河上來到楊柳青,可以說,楊柳青借着運河彙集了南北建築的精華。
運河邊的美食和文化
黎記包子是楊柳青傳統美食的代表,傳說中的楊柳青黎記包子有多好吃?雖然黎記包子已經停業,馮立找到了掌故老人,知道了黎記包子的特殊配方。
對楊柳青曆史的研究中,美食是不可略過的部分。史料記載,楊柳青的飲食業起自元代,當時沿河兩岸設有飯攤,零售糕餅包子等類食品,為過路行旅打尖食用。自明永樂年後,楊柳青的茶肆酒樓更是鱗次栉比。
在馮立的記憶中,西渡口對面有一條因經營飲食業而得名“飯店”的一處街市,黎記包子最早就在西渡口胡同的西南角。當年的黎記包子門庭若市,很多市裡人專程跑到楊柳青吃黎記包子。當年的孫記酥糖更富盛名,購買要排長隊,同樣是楊柳青美食的代表。
如今,黎記包子已經停業,孫記酥糖被打工的王家人傳承下來,楊柳青酥糖至今保留着傳統工藝,是楊柳青的著名特産。
美食代表着楊柳青繁盛時期的物質豐富,楊柳青的文化更是異彩紛呈,國術家、評書家、詩人……楊柳青名人輩出。
“當年的楊柳青有很多書場,可見評書藝術之盛,書場的格局和現在的相聲館差不多,楊柳青誕生了很多評書大家。”一次和評書藝術家田連元的交流中,馮立聽田連元講起了在楊柳青的故事。
1958年,田連元到楊柳青說書。此前,他的表演得不到觀衆認可,觀衆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時候三四位。田連元曾幾次試圖轉行,來到楊柳青說書後,每天能有四五十人聽他說書,楊柳青人對評書的喜愛讓田連元有了自信,從此,他在評書藝術道路上越走越遠。
楊柳青的美食、楊柳青的文化在馮立的研究中逐漸清晰,楊柳青的民俗更是馮立最深的記憶。
楊柳青花會
楊柳青的花會是20世紀80年代春節的一大特色,每年春節,馮立最喜歡的活動就是趕廟會,開廟會期間,正是各種花會表演的最佳時機,“正月十四到十六,各道花會旌旗招展,龍燈、獅子、碌碡、高跷、法鼓,在楊柳青各條街道巡演,一陣鑼鼓剛過去,一陣吹打又過來,簡直鬧翻了天。街道上、牆上、房上都站滿了人。”
而今,楊柳青花會仍然是元宵節的天津特色,全國到楊柳青觀光過節的遊客越來越多,楊柳青的花會也逐漸走向全國,為大家知曉。
重溫運河的曆史,輝煌燦爛,在曆史中回望楊柳青的過往,作為楊柳青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指揮部辦公室文史組副組長,馮立對楊柳青的未來充滿期待,“傳承和利用好大運河文化遺産,開發大運河文化旅遊精品,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楊柳青的未來無限風光。”(津雲新聞記者 勞韻霏)
【千問千尋大運河】300年前來到天津 運河饋贈的“緻富經”
11月底,寒潮剛剛過境,冬小麥長出一片毛茸茸的綠色,北方已進入農閑,但天津市西青區辛口鎮小沙窩村裡的農民正迎來一年中最繁忙的時節——沙窩蘿蔔季。
京杭大運河南運河段緊貼着小沙窩村流過,雖已沒有昔日繁盛的景象,但小沙窩村人一直感念着運河的饋贈。是運河的沙和水孕育出了沙窩蘿蔔特殊的口感,那口汁水迸濺的碧綠脆爽是小沙窩村人世代流傳的冬日記憶,也是小沙窩村乃至整個辛口鎮的緻富“金鑰匙”。
執拗的青蘿蔔
大運河沿岸在約600年前就有了村落,據宋史記載,為防禦契丹,朝廷在大運河沿岸設沙渦砦,明成祖定都北京後,大量移民遷入定居開墾,沙渦逐漸演變為沙窩,曾經的軍寨慢慢發展為村鎮,辛口鎮的小沙窩村便是運河邊最早形成的村落之一。
沙窩蘿蔔是何時開始在小沙窩村種植的,這個問題已不可考。“應該是早期在這裡駐紮戍邊的軍民先開始種植的,大面積的種植是在約300年前。”天津沙窩蘿蔔文化體驗館講解員高海林說,“沙窩蘿蔔的種子可能也是這些軍民帶來的。”
從品種上來說,沙窩蘿蔔隻是普通的青蘿蔔,沒有什麼特别之處,但當這粒平凡的種子被埋入小沙窩村的土壤裡後,神奇的變化開始産生。
大棚裡成熟的青蘿蔔
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重印(明清)的《靜海縣志》記載:水蘿蔔有紅綠兩種,紅者春種夏收,綠者夏種秋收,皆生食,如水果類綠色者以沙窩良産。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清朝時,沙窩蘿蔔的優越性已經十分突出。
離開限定産區,沙窩蘿蔔就變了味道,這是一棵青蘿蔔的執拗,它很挑剔,隻有提供令它滿意的土和水,它才願意以美味回報,小沙窩村的水土符合它的要求。“曆史上黃河多次泛濫,黃河水也曾流經辛口鎮一帶,河水中的泥沙日積月累沉澱在此處,形成了上沙下黏的特殊土質,因而種出的蘿蔔非常好吃。”高海林說。71歲的小沙窩村村民董乃智記得,他小的時候,村旁的運河河道裡流淌的仍是黃河水,他和夥伴們在河水裡遊泳戲水,生活用水也取自運河,“那個水澆完地以後,表面會留下一層薄薄的黃色,那就是黃土高原的土。這樣的土除了适合種蘿蔔,還特别适合種瓜,我們村夏季種羊角脆、博洋九,也都很好吃。”
從種到藏 都是非遺
小沙窩村幾乎家家種蘿蔔,但家家的方法不盡相同。
選種是種植的第一步。蘿蔔種子由各家自己培育,代代相傳,選種的方法近似祖傳技藝,不能輕易示人。董乃智從幾歲起就跟着祖父種蘿蔔,選種的方法也是祖父親自教他的,“蘿蔔選好看的,上下勻稱,開的花要大小适中。”更多的方法,董乃智不再透露。
沙窩蘿蔔屬于管理型農作物,種植手法直接影響作物品質。普通種植的青蘿蔔大部分肉質根都埋在土壤裡,但正宗的沙窩蘿蔔成熟後絕大部分肉質根位于土壤以上,為翠綠色,口味脆甜,末梢幾厘米紮在土壤裡,為白色,味辣,拔出蘿蔔後地上留下一個錐形的小坑。成品蘿蔔以“小白根”為上乘,白色部分越短,蘿蔔好吃的部分就越多,這種特殊的生長形态正是人為幹預的結果,“蘿蔔多大部分在土以上跟撒種深淺沒關系,你問具體怎麼種,誰都不會告訴你。”董乃智笑着說。
村民在自家的大棚裡
沙窩蘿蔔的生長期約為3個月,陸地種植于立秋前後三天播種,霜降前後收獲,拔出來的蘿蔔不着急上市,先存在地裡,待到入冬,天津衛的茶館、澡堂、戲園子都要開始供應沙窩蘿蔔,那時才能賣個好價錢。董乃智仍記得他小時候随家中長輩去紅橋小西關一帶賣蘿蔔的情景,天津衛的吃主們都是内行,好蘿蔔摔開一個,後面都不愁賣。
埋在地裡的沙窩蘿蔔能一直賣到臨近春節,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沙窩蘿蔔能夠始終保持新鮮的口感,得益于它的儲存方式。“藏蘿蔔的坑挖在地邊,一米深,五尺寬,放50公分蘿蔔,埋50公分土,天冷再加點土。因為土質好,蘿蔔存在裡面不凍不糠,最長能儲存到清明節都不壞。”董乃智說。
2009年10月,沙窩蘿蔔種植與窖藏技藝入選了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現在,沙窩蘿蔔已基本不窖藏,借助先進的農業技術,待拔的沙窩蘿蔔可以一直種在地裡而不會熟過頭,這個過程被稱為“活體儲糖”。
蘿蔔經紀人
每年11月18日是辛口鎮的沙窩蘿蔔開拔日,一年一度的“沙窩蘿蔔節”也在這一天拉開帷幕,迄今已舉辦14屆。開拔日後,進出小沙窩村道路的沿線都會看到售賣蘿蔔的攤位,小沙窩村裡的成片的種植大棚紛紛卷起保溫的苫布,農戶在大棚邊擺上采摘的廣告牌子,老人們坐在齊牆高的蘿蔔包裝箱下聊天曬太陽,年輕人忙着給蘿蔔裝箱打包,空氣中撕扯膠帶的聲音此起彼伏,整個村子,都在圍着蘿蔔忙碌。
大棚外打出的采摘廣告
郭芝建的合作社裡人來人往,倉庫裡存着5萬斤今年新下來的沙窩蘿蔔。“也就夠賣10天的。”老郭說,“現在一天就走5000斤。”62歲的郭芝建原本也隻是小沙窩村的普通農民,家裡世代種蘿蔔,但現在,他有一個更時髦的身份——蘿蔔經紀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沙窩蘿蔔都是以外銷為主的特殊商品,上世紀三十年代,沙窩蘿蔔主要出口日本和東南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沙窩蘿蔔主要出口新加坡,還有一些會賣到我國的香港地區。大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沙窩蘿蔔才開始轉向主銷本土市場。很快,村裡就出現了商販的身影。“有的販子騎着自行車,到各家的地裡去看,因為各家的蘿蔔品質都不一樣,販子們要親自去挑選,看中的才談價收購。”郭芝建回憶。
老郭在他的倉庫裡
老郭家的蘿蔔是村裡的翹楚,他的父親郭桶年曾任生産大隊技術員,參與過上世紀八十年代沙窩蘿蔔種子提純複壯工程,郭芝建曾任過生産小隊的技術員,他喜歡鑽研,通過觀察和實驗,不斷改進着沙窩蘿蔔的種植方法。起初,郭芝建和其他村民一樣,隻種蘿蔔,然後等着販子來收,随着銷量的增加,郭芝建自己種的蘿蔔已經不能滿足與他對接的商販的需求,于是他開始在村裡挑選其他種植戶的蘿蔔供貨,再後來,郭芝建幹脆自己成立了合作社,當起了蘿蔔經紀人。
蘿蔔還種在地裡的時候,郭芝建就會去村裡挨家挨戶地轉悠,誰家的蘿蔔什麼品質,他心裡早早有了數。收成好的年份,他不用親自去地裡收蘿蔔,趕上歉收的年份,好蘿蔔尤其稀罕,有的蘿蔔經紀人甚至會去地裡蹲守搶貨源。“今年就是賣方市場,産量低,但是蘿蔔好吃,我的手機從10月中旬開始就每天電話不斷,都是老客戶給我打電話,問我行了嗎行了嗎,我說再等等,最好的還沒到時候。”郭芝建說。
老郭的合作社裡,正在給蘿蔔裝箱
征服南北味蕾 全鎮緻富擔當
臨近春節是老郭最忙的時候,去年店裡的快遞單子用筐裝,打包裝箱的勞工通宵達旦地工作,一天出貨約18000斤。“去年好的時候能賣到六塊一斤,八塊一斤。今年的蘿蔔貴,現在就四、五塊一斤了。”郭芝建說。
老郭的客戶早期以北方為主,尤其京津為主要市場。對于南方人來說,生吃青蘿蔔是一件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南方人更習慣用青蘿蔔做菜做湯,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南方人也接受了生吃沙窩蘿蔔,我發上海的客戶已經發了10年,還有深圳、廣州,全國各地哪都有。”
11月初,老郭為賣蘿蔔開起了直播,直播不是每天都有,隻在有空的時候才能做。11月22日那天,直播2個半小時賣了250單,銷售額過萬,令老郭十分振奮,“現在每天出貨量很大了,但還想再賣更多,賣遍全國,我賣得越多,受益的種植戶就越多,有錢大家一起賺。”
老郭的直播間
從清朝時的良産到百年前的出口專供,再到今日的網紅商品,運河水孕育的沙窩蘿蔔一直是辛口鎮最重要的經濟作物。目前,辛口鎮正在打造沙窩蘿蔔小鎮,将文旅、農旅概念引入,用好沙窩蘿蔔這塊金字招牌,為挖掘沙窩蘿蔔的經濟驅動力拓展更寬廣的領域。(津雲新聞記者 顧明君)
【千問千尋大運河】津城以西楊柳依依 運河滋養從古至今
京杭大運河由河北省入天津界,穿過靜海區便進入西青區。大運河天津段長約200公裡,西青段隻是很短的一段,全長31.3公裡,占天津河段總長不及五分之一,然而西青段大運河卻也許是京杭大運河天津段中最絢麗、最繁華、烙印最深、最富傳奇的一段。
(楊柳青運河老照片)
西青的底色,是大運河鋪就的。
考古遺址證明春秋戰國時已有先民居住在現西青境内,但因東漢時海水倒灌,海水退去後土地鹽堿嚴重,西青境内一直人迹罕至。直至隋朝開通大運河,西青界内才開始人丁興旺,沿岸居民得漁航之利,人口漸增,始有村鎮。宋代在西青設軍寨,人口進一步增加。
明清時,運河貫通南北,漕運鼎盛,西青作為南北商品的交易集散地,經濟十分繁榮。這段曆史有實物為證,沿運河走勢而建的楊柳青古鎮便是“見證人”。古鎮中有以各種交易命名的街巷,如蓆市大街、菜市大街,這種劃分與曾聯結東西的長安城相同,說明楊柳青的市集不僅穩定,而且成規模。古鎮中還有大量風貌建築,這些帶有明顯江南建築特征的院落曾是江浙富商們在楊柳青的居所。
雖然晚清時運河沒落,但營商的傳統已經根植于西青人的血脈之中。多年來,西青區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着全市名列前茅的好成績。舊時,江南的富商巨賈們雲集于此,今日,世界各地的企業聚首西青。西青區現有世界500強企業58家,國内500強企業33家,形成以新一代資訊技術、汽車及零部件、生物醫藥為代表的三大主導産業,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持久而強大的内驅動力。
(落戶西青的天津泓德汽車玻璃有限公司生産工廠中的房間)
西青的文化瑰寶,是大運河成就的。
楊柳青年畫久負盛名,2006年入選第一批國家非遺名錄,位列美術類第一名,它是西青最璀璨的文化瑰寶。楊柳青年畫自明代興起,起初隻是些門神、竈王圖案,但明永樂年間,大運河重新疏通,南方精緻的紙張、水彩來到楊柳青,與這裡匠人精湛的畫工相結合,使楊柳青年畫跨出了民俗用品的範疇,踏入藝術作品的行列。
(楊柳青年畫 瑞雪豐年)
楊柳青年畫題材豐富,格調高雅,色彩或金碧輝煌或溫潤淡雅,而楊柳青年畫之是以風靡,皇家“帶貨”功不可沒,每年都有畫作作為貢品供奉,這也令民間更加追捧。依靠運河的運輸便利,楊柳青年畫遍銷南北,而每年進貢的管道,有一種說法便是乘運河入京。
西青的精神核心,是在大運河岸邊誕生的。
著名愛國國術家霍元甲出生于西青區的小南河村,幫朋友經營位于今紅橋區三岔河口旁的懷慶藥棧,目睹列強對百姓的欺淩,萌生了“強國強種,國術救國”,雪洗“東亞病夫”恥辱的思想。今日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孱弱的面貌,但曆史的教訓仍應時刻銘記,謀求發展的腳步一日不可停歇。
運河岸邊還走出過一隊傳奇商人——大營客。因為漕運沒落,昔日的船戶為了謀生,咬牙走上了追随軍隊、遠赴新疆“趕大營”的道路,一路4000餘公裡,艱難險阻,九死一生。大營客們已不在,但“趕大營”的精神代代相傳。
大運河靜靜流淌,水面映照着四季輪回,它已完成“黃金水道”的使命,但它仍舊滋養着兩岸的土地,見證着百年曆史與新時代的巨變。(津雲新聞記者 顧明君)
【千問千尋大運河】視訊—千年運河 魅力西青
編輯:王琳 王璐
稽核:董岩 蔣麗莉
歡迎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