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後,随着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在發生改變。1888年,清政府準設算學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學納入考試内容。1898年,加設經濟特科,薦舉經時濟變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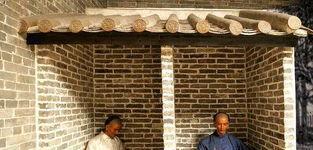
(科舉考試)
維新派對科舉一直都是持批評态度。康有為指出,八股無用,改科舉莫急于廢八股,要求“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
光緒曾在維新變法時下诏廢除八股取士,凡鄉會試和童生考試一律改試策論。隻不過變法失敗後,慈禧又恢複了科舉制。
時代的洪流是擋不住的。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釋出谕令,稱:“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别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
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又與科舉無異。曆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各門科學,尤皆切于實用。是在官紳申明宗旨,聞風興起,多建學堂,普及教育,國家既獲樹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榮。”
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來實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的終結。
(科舉放榜)
科舉制作為士民的晉升之道,一直是國家政治、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彙集點。科舉的廢除也就意味著傳統仕進之路的斷絕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科舉這樣一個重大制度的廢止,卻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反響。
科舉的科目類包括:進士、舉人、拔貢、優貢、副榜(副貢)、恩貢、歲貢、生員(廪生、附生、增生)、教習、謄錄;捐納類包括:廪貢、增貢、附貢、貢生、廪監、增監、附監、監生等等。
科舉制度不僅是一種教育制度,還是一種選官制度。清代入仕主要有科舉與捐納兩種途徑,科舉是其中最重要的選官方式。
然而清末中國士紳階層内部起了分化,由科舉入仕的比例下降,由捐納入仕的比例上升。甚至出現了捐官多于科官,形成異途壓倒正途的奇怪現象,科目正途出身者難以獲得實職。
(清代貢院)
同治元年順天府尹蔣琦齡上奏:“近日吏部選法,正途人員幾無到班之日,至有追誨不應會試中式者”。在清末捐納大開的背景下,科舉的最後自然不能引起社會的較大轟動。
科舉對普通士子來說,還是他們上升的唯一路途。科舉的廢除,學堂得到發展,“科舉廢矣,而出身皆在學堂,則入學堂既有前途之望,複無後路之歧,故入學堂者亦不患其不多。”
清政府在廢止科舉的過程中,也注重如何将傳統的功名與新式的教育相配合,使讀書人在新的學校體制中找到出路。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等人就力陳科舉之弊,提出改革科舉的主張,廢止八股取士,但随着變法失敗,這一建議并未得到有效落實。
1901年4月,袁世凱建議變通科舉,增考實學一科,經年以後,取的士多實幹之士,實學之人。張之洞與劉坤一在《江楚會奏三折》中,提出科舉改章,分科遞減科舉名額,用學堂取代科舉,并最終廢除科舉的意見,使“生員舉人進士皆出于學堂”。
他們設計了一套對應規則,國小、中學、高等學校、大學的畢業生分别對應于附生、廪生、貢生、舉人、進士。張、劉認為這是“兼顧統籌潛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礙難行”的辦法。
1901年12月5日,清廷準許了《遵旨核議學堂選舉鼓勵章程折》,正式規定學堂畢業生經考試合格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的功名出身。
(新式學堂師生)
廢除科舉使傳統士子的仕進之路斷絕,但士子獲得功名的機會比以前更廣闊了。《申報》就評論學堂本與科舉無異,學生畢業後,中學比照生員、省學比照舉人、大學比照進士,是“學校仕進并合為一”的大好事。
科舉與學校結合,則學校将大興,因為“
利祿之途,衆所争趨也”
。
科舉廢止後,如何安排舊日士子的出路呢?
慈禧也就此問過張之洞:“
若廢科舉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
張之洞認為:“
取士非由學堂不可,科舉之廢所不便者,但三四十歲之老生員耳,其年力富強者皆可以入學堂矣,且學堂大開,此三四十歲之老生員多可為國小堂之教習,又為之寬籌出路,并非科舉一停,即無事可做。
況科舉非刻下即行罷廢,其是以必待三科減盡者,亦正為此。蓋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歲矣,亦必不願再入場矣。”
正是張之洞的一番解說打消了慈禧的顧慮,“
遂面谕即與政務處妥議具奏”
(張之洞)
科舉廢止後,清政府于1906年提出有解決讀書人出路的幾條辦法:一是廣設中國小堂,使諸生入堂安心習業,二是省城設立師範傳習所,為老年諸生入學,三是高等學堂、師範學堂一律添設學額,為年二十以上諸生考選入學,國小程度未足者,令其補習。
由于措施完善,很好的解決了讀書人的後顧之憂。
科舉廢止後,清政府要求各督撫、學政“
勸谕紳士廣設國小堂,裁節官中不急用之費,捐募紳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時并舉”。
盡管士紳集團反對廢除科舉制,但是廢除科舉後,他們迅速送子弟入學堂,同時熱衷開辦學堂。如江蘇省,除了官立學堂外,其他學堂都是由士紳創辦的。
(清末新式學堂)
據清政府的統計,廢止科舉前的1903年,67%的現代學校是由官方設立的,1904年,這一數字是85%,廢除科舉後的1906年下降到37%。
私立學校的比重則迅速上升。特别是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一帶,私立學校的數目遠遠超過官立學校。僅上海一地,1906年共有125所國小堂,官立為27所,民立與私立有98所之多。
這一時期,士紳階層利用科舉廢除的機會,與官方進行合作,使下層士紳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具有“超穩定結構”的社會。
從秦漢到晚清,雖然王朝有更替,但整個曆史和文化都是連續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階層的存在。
中國人一直認為“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
,廢除科舉,不再産生“士人”,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基礎也被改變。
老照片:清末士紳富人階層家庭
随著科舉的廢止,精英和體制之間的聯系斷裂了。精英階層整體趨勢是向邊緣走,最終邊緣力量崛起。
而邊緣力量的代表——地方士紳不僅利用學堂等來為自己和宗族擷取地位,而且大量介入地方公共事務,引起地方社會的階層的分化和重組。
在科舉廢止後的士紳階層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通過學堂邁入士紳階層,這也是科舉廢止後給中國階層帶來的新的變化。
參考資料:
《奏定學堂章程》、《定國是诏》、謝俊美《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