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托比·利希蒂希/文 石晰颋/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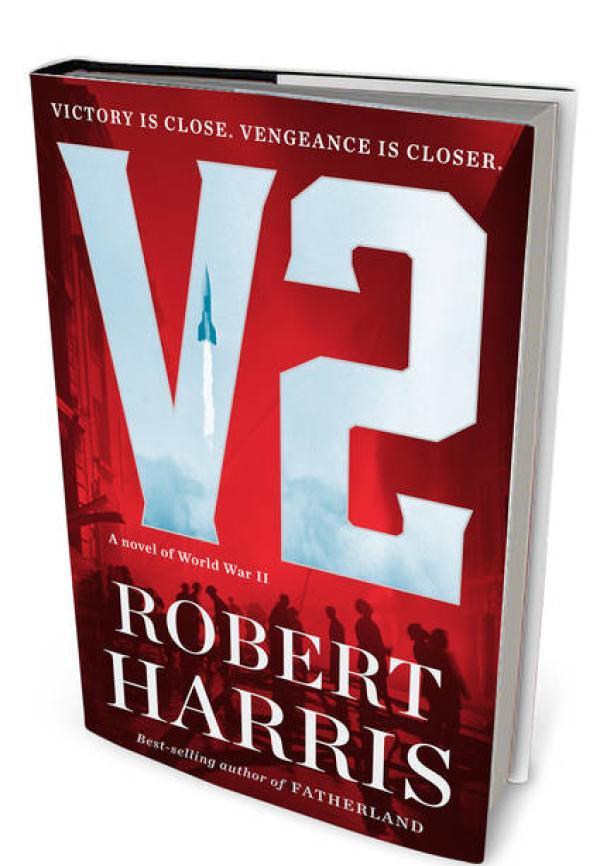
V2, Robert Harris, Knopf, September 2020, 312pp
羅伯特·哈裡斯的驚悚小說新作《V2》的結尾有一個場景,德國火箭科學家魯迪·格拉夫暗中破壞自己創造的殺傷性武器。當時是1944年11月下旬,納粹戰況告急。在絕望的孤注一擲中,他們把籌碼堆在了新的V2彈道飛彈上,從荷蘭的據點向倫敦發射了數百枚飛彈。
格拉夫解除了飛彈的機械程式,然後改動了它的無線電接收器。V2飛彈成功發射,但是,四秒鐘後,它并未向英國首都的方向以抛物線軌道轉彎,而是“她直飛向上……完美而光榮地——飛向天國”。
火箭計劃是一個巧妙而略為淺顯的隐喻,是對人類行為中所有最令人欽佩的東西的腐蝕:現實政治對科學成就的腐蝕;毀滅的沖動對學習的動力的腐蝕。它曾經是為了更為崇高的東西。現在,它的理想已經轟然倒塌,破碎一地。
這個隐喻貫穿了哈裡斯先生的小說,在格拉夫這個人物身上,作為現實中的沃納·馮·布勞恩(德國實體學家,後來上司了美國的太空計劃)的一個虛構的追随者,展現得尤其明顯。格拉夫對戰争幡然醒悟,對希特勒的政權充滿厭惡。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主管這些火箭從森林中的移動基地發射的任務。
格拉夫不是納粹——雖然因為嚴重的道德取向偏差,他也并非無辜。他不僅管理那些意在殺人的發射行動,還和他的同僚一樣熱衷于“把試驗設施和飛彈工廠建起來”。在可怖的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驅使下,這個建設項目導緻了兩萬名奴隸的死亡。格拉夫作為馮·布勞恩的某種代理人,也是探讨被玷污的理想的工具,不過他的道德骨氣比他的導師略為堅定一點兒。
哈裡斯以1982年的那部探讨現代戰争的倫理及技術的非虛構著作《更高形式的殺戮》開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的第三帝國主題小說曆程從1992年的《祖國》(虛構希特勒赢得戰争的一本架空曆史)和1995年的《恩尼格瑪》(描述英國在布萊切利園的密碼破解工作)開始。從那時起,他在文學上的努力讓我們遊曆了古代的羅馬到布萊爾時代的英國,從一場現代的教皇閉門會議到德雷福斯事件。在2017年他以一部關于慕尼黑協定的小說回到了希特勒這個主題;現在,這道弧線繼續向其起源延伸。《V2》以先進的武器、狡猾的納粹、道德的妥協和盟軍的機智為主題。
其主要情節圍繞着英國情報部門試圖通過繪制V2火箭抛物線的完整軌迹來确定其發射位置:他們有六分鐘來計算其軌迹的曲率;然後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機有大約三十分鐘的時間來沖往目标上空。
哈裡斯筆下勇敢的女主角凱·卡頓-沃爾什原本在國内前線的情報處任職,被借調到比利時的梅赫倫鎮,阻擋V2飛彈的雷達系統坐落在那裡。這部小說的雙線叙事脈絡交錯于她在代數、姐妹情誼和性愛冒險之間,也在郁郁寡歡的格拉夫與自己的惡魔鬥争時的内心旅程中切換。整個故事(除了尾聲)在五天内展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發生的事情不多。火箭的一次次發射以可親的筆觸描寫;它們落地或誤射。凱抛棄了一個在布賴特的不忠的情人,并與她的比利時房主糾纏在一起。格拉夫和他的團隊被一個黨衛軍人拜訪。故事裡這位科學家的良心危機來得正是時候,導緻了他進一步破壞自己的工作,接下來還有一場嚴厲的審訊與清算。他後來堅持了自決權。最後的一個轉折與凱有關,是我們能預見的一個曲線。
書裡還有不少背景故事。事實上我們還會讀到,有七十頁的篇幅都是關于可惡的卡姆勒和他的火箭工廠。格拉夫的大部分叙述都涉及到他對之前黨衛軍審訊的回想,以及他對與馮·布勞恩在一起的光陰的回憶。凱的故事戛然而止。那些熟悉“十字弓行動”的人都知道,這種抛物線戰略徒勞無功。
哈裡斯對如此單薄的素材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凱和格拉夫的形象都很有吸引力,盡管有一點似曾相識的重複感。小說的節奏良好,行文輕快,雙重叙事結構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起到了推進作用。戰場故事的場面排程十分到位,從梅赫倫總部令人反感的魚肉混合醬三明治,到凱的雙倍彈性“激情殺手”内褲;從乘坐達科他運輸機旅行的不适,到格拉夫和他的同僚們能得到面包卻得不到洋芋的觀察:他們國家的洋芋作物都被用來生産火箭燃料。
在道德上這本書也很簡單。格拉夫這個良心不安的角色設計很容易激起我們的同情心,他的悔恨也許來得有點太輕易了(“他想,我的上帝啊,我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啊?”)。更有意思的是外圍角色中的馮·布勞恩(“他總是能把别人的悲劇納入自己的步調裡”)。納粹大多是卑鄙的,不過作者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們,英國人也在進行偷偷摸摸的宣傳,而英國皇家空軍的一次空襲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幾乎是V2飛彈的十倍。
我們的文學文化是否需要再來一部這樣的二戰驚悚小說這個問題值得考慮,尤其是這種在對立面之間不露痕迹地雜耍的作品。然而,假設确實有此需要,那麼讀羅伯特·哈裡斯的作品肯定不是最壞的選擇。
(原文發表于2020年11月12日《華爾街日報》,經作者授權翻譯發表)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