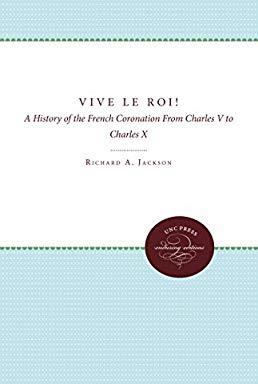
國王萬歲!從查理五世到查理十世的法國加冕史
法國的加冕禮有着歐洲最為悠久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時期的查理曼加冕禮。法國人Godefroy早在17世紀便出版了一本收錄了大部分重要加冕禮記錄的作品Le Ceremonial de Français,從這一角度來說,在加冕儀式的記錄上法國人要早于其近鄰英國人。在18世紀以後對于儀式與王權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特别是加洛林早期查理曼的加冕儀式以及波旁後期絕對君主制時期的儀式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而此前的研究則要少得多。到了1984年,理查德 A.傑克遜(Richard A.Jackson)教授的作品《國王萬歲!一部從查理五世到查理十世的法國加冕禮史》(Vive Le Roi!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Coronation from Charles V to Charles X)成為了一本難得的涵蓋了中世紀中後期到大革命之後最後一次加冕儀式的作品,這對于此後法國加冕禮研究都有着獨特的貢獻。
古本手繪的法王加冕儀式
上左:護送聖膏油瓶,上中:塗油禮,上右:披上王袍,左下:衆世俗貴族代表與教會代表一同将冠冕置于國王頭頂,右下:教會代表在歡呼聲中向國王宣誓效忠。
從9世紀開始的法國加冕儀式就融合了宗教與世俗兩種要素:即塗抹聖膏的塗油禮與戴上冠冕的加冕禮。法國人十分重視這類國家慶典的儀式性,就像英國人重視其憲政性一樣,法國人将塗油加冕禮視為"王座與聖壇的結合"以将法國王權與教權聯合起來,"即使到了啟蒙運動時代也不允許對于加冕禮的貶低"以至于"法國的加冕儀式一直延續到了1825年",這是其他國家儀式(葬禮、進城禮和君主莅臨高等法院儀式)沒做到的。在讀起這本書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傑克遜教授有意引導讀者按照時間順序來了解法國在從中世紀王權向絕對主義王權建構的過程中是如何一步步追求王權的絕對性的,這也是傑克遜教授在最後想要說明的。
路易十三:波旁王朝第二位國王 ,三十年戰争中帶領法國成為新的歐洲霸主
全書分為五大部分,起筆并非書名所說的查理五世而是極富典型性的路易十三加冕禮,而後再從查理五世時期加冕禮中的變動娓娓道來,從王權的有限性講到追求和實作絕對君主制時期加冕禮的變動,而後則是大革命之後以拿破侖為代表的君主們如何整合加洛林時期和波旁王朝加冕禮特征與大革命時期的新的政治特色相結合,最後一章是結論章,傑克遜教授指出一部法國加冕禮的曆史就可以看成是法國王權演變的曆史,從中世紀到文藝複興,再從文藝複興時期到絕對君主制,從絕對君主制時期到大革命之後,加冕禮在法國延續近千年,見證了法國王權的興衰。通過最後的點題,傑克遜教授也給出了加冕禮研究的意義:通過儀式來反映王權變化,甚至了解從中世紀王權到絕對君主制理念的變動,都不失為一種突破口。
查理五世加冕圖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傑克遜以路易十三的加冕儀式開篇,然後轉向介紹法國加冕禮儀書撰寫的轉變。他指出"一些加冕儀式是對此前加冕禮的單純的模仿,但是也有一些會根據現實需要做出較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同樣也會凸顯在加冕禮儀書的描繪及插畫之中,如查理五世的加冕禮儀書。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亨利四世的加冕禮,"當1594年亨利四世發現因為城市掌握在天主教會手中而無法在蘭斯加冕時,他的加冕儀式改在沙特爾舉行"。這樣的轉變顯然是适應了現實的政治需求,也說明了加冕儀式絕非一以貫之。
安娜·布列塔尼:布列塔尼公國的所有者,因其婚姻決定着布列塔尼公國的未來,她成為各國争奪的對象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傑克遜讨論了加冕誓詞和其對皇室權力的限制性。在近代早期确實可以從誓詞中看到對王權的限制,比如"王權不可轉讓的加入,綁定了國王與他的國家,讓這個國家的财富與領土不能被送出。"值得一提的是國王與國家婚禮的儀式,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隐喻。這種結婚的隐喻最早出現在加冕禮上并不是在國王的,而是在皇後的。在1504年安娜·布列塔尼于聖丹尼斯皇家修道院的加冕禮上,一份記述寫道"加冕者将戒指戴到了她右手的第一個手指上,這個通常戴婚戒的手指意味着她嫁給并掌控了法蘭西王國"。這一儀式是否和教士授職儀式上的宣誓有關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切地說正是安娜的加冕禮将國王與國家的婚姻隐喻帶入了加冕儀式。
康托洛維茨:其《國王的兩個身體》被譽為20世紀學術史上的一個神話
在康托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也提到,這種說法特别是在讨論國庫财産不可讓渡性的時候被法學家運用。他認為到1300年的時候這種情況可能就已經非常普遍了,康舉出了那不勒斯法學家盧卡斯·德·佩納在十四世紀中期撰寫的《法典》最後三卷注釋中認為,君主就是"國家的丈夫"(maritus reipublicae),他主要是要證明一項基本法則:國庫的财産不可讓渡性。是以他将國庫解釋為新娘的嫁妝,并解釋說丈夫有權使用妻子的财産并且不可讓渡。
第三部分傑克遜談論了儀式如何展現的王權趨向于絕對化。無論是沉睡的國王儀式還是王室血脈高于一切其他貴族的法理學論證,都是在展現王室權威至高無上。不同于在理論上建構國王兩個身體的英國人,法國人更傾向于在儀式上展現這一理論。
世界名畫:拿破侖一世加冕大典,現藏于巴黎盧浮宮和凡爾賽宮(各一幅)
第四部分則讨論了大革命以後加冕禮的變化。遺憾的是,我們看到很少對于拿破侖一世加冕禮的介紹,因為這本該是一場具有時代意義的加冕儀式。拿破侖一世的加冕禮結合了加洛林、波旁王朝的傳統,同時增加了大革命時期的許多民族特征,極力渲染其民族性和帝國性,這與專制主義時期的加冕儀式是有所不同的。從大革命後的儀式變化也能看出,文化的改變可以透視政治的變遷。
與大多數作品一樣,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是結論章。傑克遜教授将之命名為"王權的隐喻"也就是加冕禮。他回顧了中世紀早期法國加冕儀式的起源、國家神話的創造,然後逐漸引出絕對主義在法國加冕禮中的反映。傑克遜極具創造性地提出一點,那就是在中世紀君主制與絕對主義君主制之間實際上有一個過渡階段,這一點從儀式的變化上就能反映出來。
遺憾的是傑克遜沒有将這一點與另一名著名制度史研究專家J.Russell的"文藝複興君主制"概念結合起來,否則這不失為我們了解文藝複興時期法國君主制度的一種新角度。
查理十世:名查理·菲利普,法蘭西波旁王朝實際上的末代國王和倒數第二位國王,波旁王朝複辟後的第二位國王
傑克遜的書中明确描寫了1364年到1825年之間法國史上許多重要的加冕禮時的情況:如将王權不可轉讓(Inalienablity)加入到加冕禮宣言誓詞中的查理五世加冕禮(1364年);查理八世加冕禮對于聖人雷米(Saint Remigius)作為國家的仲裁者以及法蘭克傳奇上司者法拉蒙(Pharamond)是國家法律的創立者(即薩利克法典)這類國家神話的追認 (1484年);将加冕誓詞中排斥異教徒的段落删除、引入國王戴上戒指的隐喻(即國王通過戴上戒指迎娶國家,強調了王權不可轉讓的概念)、進行加冕後的國王施舍以及選舉性王權概念的加入(1547年亨利二世加冕禮);1563年最初的"沉睡的國王"儀式的舉行(查理九世);1576年以後王室血脈高于其他貴族的觀念(亨利三世加冕禮之後);1594年亨利四世加冕禮中國王與國家的婚禮隐喻的進一步發展(國王向國家索要"陪嫁"和領地);1654年在加冕誓詞中加入國王是聖靈的守護者的條款(路易十四的加冕禮);路易十七、路易十八加冕儀式的失效和拿破侖一世作為帝國君主的加冕禮;還有查理十世持有憲法進行加冕的法國史上最後一次加冕禮。
所有上述這些加冕儀式都強調了其"變"的特性,也就是每一場加冕儀式都有着獨特的時代背景,因而想要與前人有所不同的君主們才會通過儀式的變化來反映自身的追求。以1364年的查理五世加冕禮為例,查理五世加冕于英法百年戰争的第一階段,法國剛剛戰敗不久,國内出現紮克雷起義等動亂,王室權威降到谷底,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查理五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加冕儀式來挽回王室形象。加冕禮在此時不再單純是國王獲得權力的儀式,而成為了一種有力的王權宣傳的輿論工具。
查理五世加冕禮儀書中的插畫
傑克遜教授在書中十分肯定地指出了加冕儀式在不同君主時期的變化都吸收了過去的傳統,由此引出了他對于王權演進模式的解讀。他給法國王權劃分了四大特征:有限的(limitation)、王朝的(dynasticism)、宏大的(grandiosity)以及"展現王室權威的變種"(mutations in the expression of royal grandeur)。
不過,傑克遜教授的著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最為明顯的就是在一個章節中對于"沉睡的國王"這一儀式的論述,傑克遜教授将沉睡的國王與中世紀騎士的沉睡儀式聯系的實在有些牽強。而"沉睡的國王(the Sleeping King)"儀式在其他作者的書中往往都隻是與國王的兩個身體這一王權概念聯系。在吉爾斯(Ralph E.Giesey)的<Rulership in France, 15-17 Centuries>一書中也提到了和傑克遜完全一樣的例子,即路易十三在自己的加冕儀式中假裝沉睡地躺在自己寝宮中的"王國之床"(bed of state)上,用來展現路易十三的自然身體與神聖身體是分開的。
就在馬車停下的間隙,一個紅棕色頭發的男子突然沖進馬車,迅速地用刀刺中了亨利四世,這讓他措手不及!
由于亨利四世遇刺身亡,他的幼子路易十三八歲時不得不即位,是以王室想出了這樣一種儀式來展現國王的兩個身體,以建構少年國王路易十三統治的合法性。
這一解釋被更多的史學家所接受,而将"沉睡的國王"與中世紀騎士夜禱甚至查理五世加冕禮所使用的"王國之床"聯系起來的傑克遜教授則顯得論證地過于武斷。
當然,和其他研究儀式的專家一樣,傑克遜教授可能确實也存在過分強調儀式重要性的問題。他對于"亨利四世的成功是由于他的改宗還是他的加冕禮"的推斷以及對于"如果路易十四在更早的時候就加冕了還會不會爆發投石黨之亂"的猜想在很多史學家看來都賦予了加冕禮過高的地位。
儀式确實可以讓我們看到王權的變動,但是其重要性究竟如何把握是所有研究儀式同學應當注意的。不過盡管如此,傑克遜先生的作品仍然是具有開拓性的,甚至可以告訴我們一種結合儀式來重新探讨王權演進的新模式,這些都有待後世的同學進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