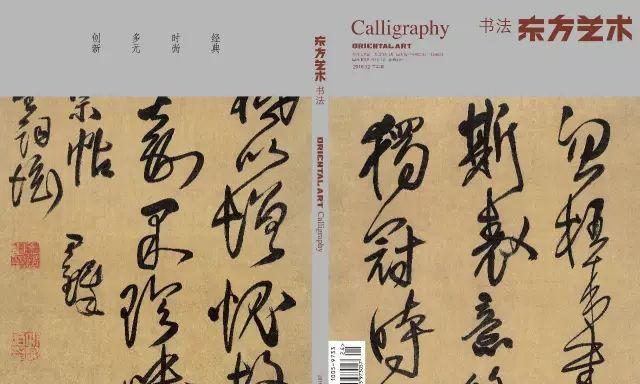
…………………………………………………………
國内統一刊号CN41-1206/J
主編:譚振飛
副主編:龍友
原載《東方藝術-書法》
2016.12下半月
獨家授權釋出
一揮便了忘工粗:
齊白石及其日常書寫
龍友
《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與《自家造稿:北京畫院藏齊白石畫稿》的相繼出版,為我們生動展現了生活中的齊白石形象,也為齊白石日常性書寫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日常生活的具體情境總是與書寫和藝術創作有着複雜的互動關系,而日常書寫的某些狀态也會不知不覺地反映到創作中,其中包括個人、群體及傳統等多方面的因素。它們間的互動使每一次随意的書寫都變得耐人尋味,是以,我們更應該把一些具展現象放回到整個日常生活與書寫的關系中加以了解。齊白石的日常書寫複雜多樣,它們一方面反映風格演進的路徑,同時又折射出他的書寫及藝術創作的觀念。在書寫與日常生活逐漸剝離的時代,為日常生活服務的書寫會呈現不同層次的日常性特征。它們的類型和層次難以清楚劃分,也不能簡單地并置在同層。本文選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現象進行分析、叙述,以期能夠提供齊白石日常書寫研究的幾個視角。
圖1 《老萍詩草》第三頁
圖2 《借山吟館詩草》
圖3 《寄園日記》封面
一、齊白石手稿中的幾個細節
北京畫院所藏的齊白石手稿,内容包括詩文、日記、書信、傳記、畫稿及雜記、賬目、藥方等,書寫時間從1903年至1936年。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據這些資料從細節而展開。
《借山吟館詩草》及《老萍詩草》都是以“金農體”謄寫的自作詩文稿,前者書寫整齊規範,是1917年左右請樊増祥删定并作序跋的自抄本;後者多處塗改、增删并雜以紀事,據題跋可知是自留稿。《借山吟館詩草》的書寫前後如一,态度嚴謹,而《老萍詩草》與之相隔四年,書體相同,書寫狀态卻有微妙變化。前幾頁在模仿金農的風格中雜糅了其他筆意,但很難作出分離,出現風格相違并不甚統一的現象。先拿第三頁來說,(圖一)墨色富有變化,書寫節奏常有細微調整,結字略感生疏,如“書冬心先生”等字瑟縮一團,下筆很不肯定。第五行“斷”字或因筆畫繁多而寫得很大,内部空間瑣碎擁擠,與周圍極不協調。整體上,與《借山吟館詩草》(圖二)的古樸渾然相比,該冊的書寫顯得突兀跳宕。究其原由,或許關乎齊白石不同階段的取法。1910年前後他改學金農、李邕,類似何紹基風格的書寫,使用頻率已逐漸降低。後來的《萍翁詩草》(1918年),書寫時間處于這兩種詩稿之間,業已脫去何紹基的風格影響。結體也明顯帶有向右攲斜的趨勢,可見李邕行書的某些元素在他的日常性書寫中已是揮運自如。當他再次用“金農體”謄寫《老萍詩草》時,其他筆意自然在無意識間幹擾,轉折的方硬和筆力的強化,使其無法保證書寫風格的純粹性。這種交錯的現象,不僅展現在日常性書寫中,此時繪畫的落款風格也早已易轍。
1909年所書的《寄園日記》,尚處在學習李邕的初期,封面自題“寄園日記,乙酉重遊廣州”(圖三),字形、筆意亦步亦趨,幾乎是從李邕碑刻中原樣翻出。同年三月在廣西所作的《鹌鹑寫照》畫稿(圖四)左側題記“乙酉三月,客東興為鹌鹑寫照”等字,也是謹守李邕法度,書寫極為小心。日記前幾頁謹慎地保持近似李氏風格的書寫,第10頁開始則慢慢出現差異,不時流露出齊白石早期的書寫習慣,到中間即呈現遊移未定,多種筆意交雜的狀态。再如日記第44頁前後的筆意都處于融合狀态,這一頁卻突然嵌入标準的李氏書風,其相似度猶如實臨。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一特殊現象的産生,或是要特意表達什麼情緒?審讀文意得知:就在前一天,齊白石從朋友處得到亡友嚴鶴雲手書對聯,雖未署款卻是“自藏篋底”的得意之作。他面對亡友的遺墨,内心深感“故人平生與餘之情重,學書之工苦”,連夜在枕邊作好題記,次日一早便謄寫到對聯上。因為兩人的交誼與書法的不解之緣,他選擇标準的李邕體作題跋,可謂意義非常。那麼,順着書寫的慣性将事件和跋語同時寫入日記也變得自然。創作意識的延續,前後幾天内書寫的明确區分,打開了研究齊白石書寫中層次錯雜問題的友善之門。(圖五)來自前人的不同筆意,經過十幾年的磨合,最終都要有所棄取。他逐漸舍棄何紹基、金農、魏碑等的形模,又将李邕書風的某些特征熔入到自身的書寫習慣。
圖4 《鹌鹑寫照》畫稿
圖5 《寄園日記》第44 頁
圖6 《緻姚石倩》手劄
圖7 行書信劄局部
圖8 走字底示意圖
20世紀20年代,我們又很難在他的手稿中見到恪守李邕風格的書寫,稿本封面也不再刻意與内文差別,但這并不意味着他的創作意識在手稿中消散,而是随着情境的轉換,不同僚件和情緒,都可能将看似整體不變的日常性書寫分化成不同層次。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像之前那樣明顯改變取法方向,而進入到完善“自我”的階段。日常性書寫作為生活和創作(包括繪畫題款)的附庸,不斷從創作中獲得新資訊,通過重複的書寫而成為另一個完整的書寫系統,但兩者又非泾渭分明,而是若即若離。有趣的是,齊白石日常性書寫中的某些變化總比創作晚一步,同時又有另一部分細節特征始終在兩種書寫中保持。要叙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選擇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率極高的單字或字元作為考察對象。這些常用字猶如書寫者的姓名一樣,在長期的書寫中必然形成個體化偏好,并為研究書寫相關問題的标本。
且從“得”字說起,該字右部書寫一般都作“ ”,齊白石早年也大多使用這種寫法。與何紹基風格一脈相承的《癸卯日記》(1903年)和《行楷立軸》(1909年),“得”字寫法出現行書和草書交替,右部都作“ ”,并無特别之處。他于1920年4月寫給學生姚石倩的信劄中共三次使用“得”字,右部卻都寫成“ ”形,(圖6)在同期的繪畫題跋中也是如此。而且每次遇到都刻意寫得稍大,看起來總比較顯眼。通過比較發現,這種現象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創作中逐漸穩定。這一獨特偏好,在他同時或更早的手稿中,并未完全得到普及。當他1922年書寫《壬戌紀事》時,開始出現新舊交替,而創作中“ ”形寫法卻早已完全定形,并一直保持到最後。(圖7)将創作中形成的某些偏好變成日常性書寫的習慣,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轉換。
書法創作或題跋的書寫,要具備供人玩賞的功能,才能被認可。而日常性書寫與寫給人“看”的書寫之間,往往因自覺意識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形成差異。當書寫者進行創作時,總希望将“好”的一面展示給觀衆,一切“新奇”的東西都可能被使用。它們不僅代表着書寫者日新月異的良好狀态,也可能是以與前輩和同輩藝術家一決高下。日常性書寫需要從創作中汲取營養,利用習得的“新”方法,改造這座由習慣性書寫堆積而成的堅固堡壘。當齊白石習慣性地把“得”字右部全部替換成“ ”形,那就意味着,日常性書寫獲得了一次成功的改造。每一次替換都可視為書寫演變的一個轉折點,在“選擇——接受——形成習慣”的邏輯中,必然隐含着某一個重要的契機。對齊白石而言,遠遊歸來、定居北京都面臨太多挑戰和塑造“自我”的機遇。他必須重新審視并逐漸調整每一個細節,使創作變得“新奇”而又耐看。“得”字的變化或為其中的一個标志,因為在帖學傳統中,很少使用這種結字方式。回望明清以來盛行的金石學風氣,許多文人書家把篆法引入楷書和行書的創作。刻意求奇成為一種風尚,從徐渭到揚州八怪,幾乎達到極緻。齊白石似乎有着與生俱來的自新意識,他的目光總是停留在這些富有創造力的前輩藝術家身上。無論繪畫還是書法,都是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塑造“自我”。從他作品中“辵”部寫法的不斷調适,似乎可以想見自塑過程的内心糾葛。
圖9 《癸卯日記》第22 頁
齊白石手稿及創作中,“辵”部幾乎貫穿每一次書寫,不同階段的變化有着明顯的規律性。雖然姿态各異,但依然可以按照形态特征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簡省為一筆,作左下部彎折狀;第二種是“辶”部原型或稍作簡省,但簡省的程度不大;第三類與第一種基本相似,隻是彎折的橫縱兩個方向的夾角從90度左右變成45度左右。第一類多為平收筆,後兩種收筆則大多向右側作雁尾狀挑出。此外,還有首筆作“弓”形連續彎曲,與篆書寫法相近,但極少使用,在日常性書寫中幾乎不用。(圖8)1903年《癸卯日記》的書寫,(圖9)呈現何紹基手稿書寫的典型風格,與同時期的創作、題跋非常一緻。其中“辵”部的書寫始終保持第一種類型,這種寫法與何紹基可謂一脈相承。書寫《寄園日記》時,前幾頁第一類和第二類混用,第八頁以後完全回歸第一類。說明這一習慣在六年間沒有絲毫改變,即使在前幾頁已經意識到,那也抵擋不住習慣性的動作。而這時的創作,卻已經完全過度到第二種類型。1918年的《萍翁詩草》,前兩頁都作第二種類型,但随着事件推移,又漸漸回到第一種類型,并一直保持。在1921年所作的《行書條幅》中,出現四個“辵”部的單字,其中“還”、“遍”、“過”三字為第二類寫法,“遇”字為第一類;與同年所作的《白石雜作》比對發現,盡管這一時期的創作已經普遍使用第二種類型,但日常性書寫卻都停留在第一類。1923年所作的另一件《行書立軸》中,“辵”部共出現五次,有四次使用第二種類型,隻有一次保持第一類。直到兩年後的《白石詩草》系列手稿中,才部分出現第二種類型,大多數還是保持第一類書寫。就此而言,這一時期齊白石的大多日常性書寫,還沒有得到來自創作的具體回報,而同期的一些書信中卻又大量使用第二種寫法。第一類的書寫确實較為順手,尤其适應匆促的日常性書寫。但如果僅僅因為便利而導緻書寫不同層次的分化,那麼“得”字的同步推進現象便成為一個特例。
在複雜交錯之外,一部分單字的形态,卻在齊氏的書寫中從未有過改變。如“存”、“在”二字的寫法始終如一,也與何紹基一脈相承。在何氏的手稿中,此字左上部“橫—撇—豎”的書寫順序都作“橫—豎—撇”。這一寫法打破了“二王”經典體系的一貫性原則,将篆隸“從才從土”的結構直接運用到行書,這一“新奇”的寫法被晚清以來的文人普遍接受。從根本上來說,“存”、“在”等字的寫法在他眼前現有的形式體系中,已屬最“新”而不太可能被超越,無需進行改造。齊白石書寫中,不斷處于變化的單字畢竟隻是小部分,因為對字形的改造必須遵循已有的原則。文字所固有的形态限制了變化的空間,即使如此,齊白石依然在有限的空間裡反複騰挪。猶如“之”、“人”等字的寫法,在形式上已經很難找到根本突破,隻有捺畫具有表現的可能性。是以,最終在齊白石中晚年形成了向右挑出的凝重一筆,并成為他書寫的一大特征。在日常性書寫中,這一捺筆大多保持向下俯應的姿态,這樣即能便利,又能避免視覺效果與書寫節奏整體性之間的沖突。
圖10 行書手劄
圖11 《影鈎填墨鵲稿》
有意識的操控最終對書寫形成重要影響,操控甚至會成為習慣。白石晚年的創作和日常性書寫中,橫向筆畫朝右上傾斜的角度不斷增大,并趨于單一化。緻使大多單字左下角外接邊呈錐狀外形。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寫給中央美術學院校長室的一件信劄中,(圖10)“江”、“深”、“造”、“薦”、“過”、“為”、“此”、“央”、“美”、“石”等字尤為突出,這種現象在1930年前後的題跋、信劄中已經初具規模。與之相呼應的是右上角外接邊的錐尖,兩個錐尖相連,正好形成一個右上高聳的平行四邊形。尖銳的形狀被齊白石所接受并大量運用,或許與其内在精神有着某種聯系,以至于在篆書和篆刻中也常常出現。“辵”部的書寫在這一時期穩定成第三種類型,這種類型正好和錐狀外形相契,共同構成這一時期齊白石書寫的重要特征之一。創作中,“辵”部的形态反複搖擺,最後回歸到第一種類型。但在日常性書寫中卻始終保持左下角彎折的形狀,這一典型書寫動作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終于對整個書寫系統産生影響。也就是說,大量重複的日常性書寫,使手部運動形成習慣性偏好,成為風格演進的重要推動因素。
《影鈎填墨鵲稿》(1948年)(圖11)的題記已是齊氏典型風格,塗改較多,墨色變化較大;書寫上前後不一,“觀之覺愁苦”之後與前段分作兩部節奏。“人”、“之”等字的捺腳基本定型,幾乎沒有向下反收的動作。“今”字下部的反寫,似與“得”字寫法同樣值得注意。作于1928年《仙鶴》立軸的第二段題記中“今”字反寫,與篆書某些寫法一緻。現藏成都博物院的《紅樹青山圖》題款“辛酉冬,白石君畫于借山吟館”中的吟字“今”部也作反寫,此畫比《仙鶴》圖早七年,另在1917年所作的《戲拟八大山人》圖中的三個“今”字中有兩個反寫,從交替的現象中,大緻可推定這一習慣的形成時間。這種現象在同時期的日常性書寫中是否也同步出現呢?查齊白石1920年《庚申日記并雜作》第四頁記初十日事中,“今”字并不作反寫,第五、六、十、十四諸頁中也是正常寫法。書于1921年的《白石雜作》中“今”字都作正常寫法,而“得”字卻已經基本形成右部為“ ”的習慣。在1932年以前的各類詩稿中,盡管“得”字正在悄然發生改變,而“今”字卻始終保持着正常寫法,即使信件的書寫也是如此。
在齊白石的日常性書寫中并沒有像“得”字一樣将某些特殊性書寫貫穿始終,而隻是在“認真”的創作或題跋中普遍使用。“辵”部在創作中大多寫的完整豐富,而日常性書寫中卻始終一筆帶過,直到晚年才日趨合一。從書寫便利的角度來說,“今”字反寫,辄意味着放棄流暢的筆勢,而追求奇異的節奏。這一追求在形式上可以獲得“新奇”的效果,同時卻大大地抑制了自然揮灑的空間。這“新奇”的篆書字法篆刻中大量使用并不奇怪,而把這一寫法引入行書中便成為一件奇事。為了獲得奇特的效果,他并不在乎書寫的流便。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他資源在他筆下為“奇”所用,即使不那麼恰切,卻已經足夠展現符号化的意義。猶如他的畫稿,反複“制作”為的是最終達緻造稿的“自家”觀念。複雜交錯和始終如一的混合現象說明,為日常生活服務而進行的各種書寫,本身包含着多種層次,每一層次都根據不同的需要選擇合适的書寫方式。相對變化的部分,日常性書寫往往滞後于創作。其主要原因,或許在于書寫者主觀上已經将不同層次明确區分,書寫活動被過度的主觀意識所操控。而日常性書寫的層次正取決于操控的程度,操控的不定性因素導緻書寫中的不同層次呈現複合交錯的狀态。
圖12 《庚申日記并雜作》第13 頁
圖13 《庚申日記并雜作》第20 頁
圖14 《壬戌紀事》第42 頁
圖15 《磚文若鳥》畫稿
二、“生活”中的書寫
研究所學生活和書寫的關系,或通過書寫痕迹解讀其與生活之間的複雜性,确是困難之舉。有意識行為和無意識目标之間關系往往并不直接,界線模糊,甚至交混一體。但我們依然可以嘗試,将齊白石的書寫與生活中某一具體事件看作一個整體,加以分析,或許可以窺見日常性書寫的外在變化與其生活境況的内在統一性。
齊白石1919年第三次來到北京并定居于此,次年二月攜三子良琨、長孫秉靈來京就學,從此開始了在京城鬻藝為生的職業生涯。《庚申日記并雜作》記錄了從1920年正月至同年十一月間的交遊、題跋、詩作及家中瑣事。從書風來看還處在何氏風格與李邕風格交融的時期,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吳昌碩行書的影響。書寫率意不拘,不計工拙,有時墨枯筆幹也不在意,塗改處滿目皆是。通讀一過,有兩處頗為奇怪:十四頁中段至十六頁,二十頁中段至二十一頁中段,這兩部分的書寫相較正本日記完全是另一種字型,明顯保留了金農體的痕迹。精緻的用筆與墨色的統一、整齊劃一的字形使之特為突兀。第十四頁中,兩種風格同置一區,相隔六天,卻奇特異常。問題是,什麼原因促使這一現象的産生?正處疑慮之時,另一個細節映入眼簾:白石在雜記的眉頭習慣以簡單的字詞作為标注,以備查找。從其他的記錄來看,注文所用的字型和墨色與正文都基本吻合,當是日記完成後順手标注。這一頁的眉心同樣如此,以較重的墨色寫了“東坡”、“鐘馗”及幾組蘇州草碼。若将正文的“東坡”及“鐘馗”等字與注文相較,書寫風格相差何啻于千裡,無意間為精緻的正文露出了“馬腳”。(圖12)有一則故事曾說米芾寫小楷詩稿,篇幅很長,前後如一,與平時的作風大相徑庭,要不是偶然露出“故态”真是難以辨認。白石此處眉批小字的随意便露,是他所沒有預計的事情。這一小小的資訊,卻告訴我們,當他完成一天的酬應再來記錄繁雜的日常事務時,很難再經意于書寫,但是偶然一次特别的事件或一種可人的心情會勾起他對于書寫的興緻,精意求工便是順其自然。另一段夾在八月二十九及二十五日間書寫整齊的日記,記錄了二十八日跋梅蘭芳書法的全文及緣起:姚玉芙結婚當日,白石應邀前往喜酌。當他到時,梅驚叫道:“齊先生來了。”白石頓時大為驚異,感激梅氏“知餘淪落而不相輕”的不棄之情。(圖13)于是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經寫成一絕:
記得先朝享太平,草衣尊貴動公卿。
如今燕市無人問,且喜梅瀾呼姓名。
這一事件已在七月二十一日中記載,但書寫十分草率,詩句的塗改很多。後接前文提到的十四頁中段至十六頁大篇幅日記,記錄自作題畫詩跋。這一風格跳躍的現象是否與相遇梅蘭芳事件之間存在關聯已無明證,但是白石本人對于這段交遊的經曆一直銘記,以至于在以後的詩稿、雜錄裡屢有提及。詩句“布衣尊貴動公卿”看似回憶往事,實際是借前朝以優厚待之的朋舊喻之梅氏。按照日記記載,正愁“無人問”時,尚有姚玉芙、梅蘭芳與陳師曾等人的幫助,使他在絕境中看到了希望,感慰之情溢于言表。幾天後,齊如山要他為梅蘭芳書法提筆作跋,他又将後兩句改作“如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呼姓名”。可見梅蘭芳一語尊稱在白石的内心所驚起的波瀾,這時,或許隻有精意的書寫才能表達這份感遇之情。
他日記雜稿中還存在一些極為随意的書寫,狼藉的點畫、松散的字形與雜亂的塗抹,反映出近乎于騷動的情緒。此時,齊白石的書寫技術似乎在頃刻間全然抛棄,剩下的隻有文字的叙述,以至他在後來的補記中反複解釋這種現象。《庚申日記并雜作》第二頁記錄了他初到北京時居無定所的境況,亂離之際必然無暇顧及筆墨,是以在破筆散鋒間一派倥偬紛繁的景象。這般“淪落”的生活,衣食尚無着落,更難以激起書寫的興緻。胡佩衡曾回憶道:
……白石老人定居北京不久,常常有人請他刻印,很少有人找他畫畫。……老人感到自己的藝術不突出,非自立門戶才有出路,便立志獨創畫派,也即他後來自稱的衰年變法。
來到京城後,齊白石發現自己的畫風并不受歡迎,他那段時間複雜的情緒常常見諸詩文。雖然住所暫得以安定,也勉強可以度過暑月。但接踵而來的是,忙于酬應并為同行的兒孫解決“求師及居住”等問題;除此,還要考慮自己的作品如何才能為世人所接受。出于生計的無奈,他于當年四月初三緻信遠在四川的學生姚石倩,希望姚氏能為他的畫作在四川找到出路。急切而又難以啟齒的心情在字裡行間明确表露:
……四川如有知雅趣者,有所請餘,當盡心力以報之。士為知己死,老萍何必隻死于北京一處數人之手耳。……今年畫筆又一變,愈荒唐愈無人知,萬一有一知者真肯出錢,一難得事也。拟畫小冊子贈弟,由郵寄來,不決何時,先以奉聞。
顯然,齊白石認為自己的畫風不為人所了解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這一時期的畫法變革,對于知己的出現充滿期待。“北京一處數人之手耳”一句中“數人之手”數字為後加,可見當時在北京的“知己”确實不多,這一文字上的改動當是有所考慮的。(見圖6)此信原件共分四頁,第一頁整體略顯紛亂,改易多處,從末行開始逐漸歸于整齊,“孫輩”以下書寫進入新的節奏;是以第二頁用筆更加厚重圓融、布局平勻妥帖。第三頁開始複歸紛亂的節奏,甚至出現大量枯薄的筆觸,筆勢變化逐漸單一,從墨色及字間的承續關系來看,引文部分的書寫一筆而成,起于“四川”終于“奉聞”,中途沒有明顯因蘸墨而中斷的痕迹,“奉聞”以後又重新回到平勻妥帖的狀态。站在純形式的角度看,這一系列的變化可以說是整個書寫軸線中的自然調整,關乎于節奏和韻律。如果将事件的獨特背景和形式聯系起來,或可以推想:當他寫到關鍵的段落,心中自有難以言說的羞慚與糾結,心理活動不知不覺改變着書寫者的意識。當我們研究這些日常性書寫時,異常的心理活動與環境确實不容忽視。隻有書寫者的主觀意識離開書寫本身,或者轉移到事件或者文本表述的時候,真正日常不拘的狀态才可能發揮得淋漓盡緻。這時,情緒的變化在無意間被轉注到書寫中,并形成相對應的形态。當齊白石隻專注如何将内心的希望形諸筆端:如何既不失情面而又能表達出請求援助的内在動機。這時,書寫的品質及審美的意識已經退到幕後,成為整個事件的附屬。思緒一旦中斷,他的關注點會很快回到書寫本身的品質等問題。
《壬戌紀事》第41—42頁(圖14)中一段粗率的日記同樣引人注意,不僅反複塗改,書寫也毫不講究,直來直去,似乎瞬間變成一個缺乏基礎訓練的普通書寫者随意而書。然而,當我們仔細閱讀日記的内容,齊白石的窘境浮現目前。這段時間一直為長孫病情的危重所困擾,正準備攜老妻回鄉探視之際;三十多年至交好友郭五也值重病,“恐不能再見”。當日,掩涕向郭五拜别,“以哭孫未盡之淚大哭郭五”,次日便決定啟程。能夠保證将事件和此刻的複雜心情行諸筆端已屬于不易,精緻的筆墨表現在這種境況下似乎顯得黯淡失色,隻有這樣紛亂的筆觸才足夠訴說内心的無奈情緒。更何況,他的日記、手稿很多都是作于舟中、郵亭、驿行,或席地而書,或匆匆所為。條件的限制和事件的偶發性和特殊性,将對書寫狀态産生直接的影響。
生活的印迹就這樣在有意或無意間保留在齊白石大量的日記、信劄及畫稿中,我們可以借助它們彌合齊白石作品和生活之間的裂縫。他的生活和創作的互動關系,在日常書寫活動中被展現出來,成為了解他的另一扇明窗。再如1919年六月十八日那天,齊白石與他的學生張伯任在法源寺閑談,突然看見地上因打磨印石留下的痕迹,外形正像一隻站立的鳥。他再感歎“天趣”之餘,按捺不住用紙片覆勾出來,作為草稿儲存。(圖15)以略帶顫動且不肯定的線條勾勒帶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圖形,顯得很是得宜。當圖形不足以完整記錄這一事件,他便用跋文進一步說明,此時的書寫似乎與整個“遊戲”的氛圍融為一體。粗率而輕薄的用筆使書寫變得像這個圖形一樣得來容易,從功用的角度而言,跋文不過是圖像的注解而已。
這一偶發的事件激發了他的聯想,特定的體驗促使他用書寫記錄生活。在他的思維空間裡似乎始終裝着一個任務,就是為他的繪畫尋找别具一格的素材,即使這樣偶然的圖形也能在瞬間被他形象化。這樣的例子在他的畫稿中可謂枚不勝舉,就像十幾年後他在成都遊玩,朋友順手用蘸色的毛筆在桌案上畫下一隻蚱蜢,他覺得極為神似,立即用濕紙透印出來。稍縱即逝的有趣圖形從來沒有在他的視線裡被忽視,兩張小稿的前後呼應,似乎喻示他的藝事已經深深的融入到了生活,二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就在這有意無意間,他的情緒與書寫以及生活中的各種獨特性事件緊緊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喜劇般的日常生活。當我們小心翼翼地拆開這些網結,所看到的是,當書寫者的自覺意識不斷強化以後,書寫活動便逐漸隔絕在生活與情感之外,成為獨立的并苛求形式的表達。若想有所改觀,必須讓高超的書寫技巧成為自如揮灑的前提條件,使書寫品質不再是提筆之際的顧慮,感情才得以重新注入到書寫,把它變得有聲有色。
圖16 《蓮蓬蜻蜓畫稿》
圖17 《勾臨金冬心賞梅圖》
三、繪畫中的書寫
齊白石存世畫稿中所包含的日常性書寫大多是作為繪畫的輔助與說明,這一點前文的讨論略有所涉。然而當我們的視線注視到日常書寫和繪畫之間的相關性問題時,二者的互動關系則顯得十分重要。若要使之明晰,必須借助細緻的分析比較才可能展現出來。
齊白石從1904年開始進入學習八大山人繪畫的階段,他在一段題跋中自述了原因:
作畫最難無畫家習氣,即工匠氣也。前清最工山水畫者,餘未傾服,餘所喜獨朱雪個、大滌子、金冬心、李複堂、孟麗堂而已。璜。(題杯花)
改學八大山人最初隻是為了規避工筆畫的一些弊端,有學者認為跟他1902年至1909年間的遠遊有關。通過見聞的增加,他已經明确意識到民間畫家身上所固有的習氣。他在給楊皙子的信中說:
連年以來,求畫者必曰請為工筆。……口強答曰可矣,可矣。其心畏之勝于兵匪。
略帶牢騷的語氣中隐含着許多無奈之情。齊白石在《壬戌紀事》第十八頁中自道:本想作一張工細的畫送給朋友,因為人們總覺得工細畫大好,而自己卻深感慚愧。因畫工細的作品而自感羞慚,看起來很難了解。就像他學習八大山人繪畫多年,而在書法上卻沒有明顯取法的痕迹。或許齊白石并沒有想要當一位真正的文人畫家,但差別于民間畫家的身份必須盡快得到廣泛的認同。他非常渴望遇到藝術上的“知己”,進而跻身京城畫家的行列,成為新式繪畫風格的代表性人物并與舊式的文人繪畫區分開。事實上,現在看他模仿八大山人的一些作品,難以被人接受也在情理之中。當他再次接到工筆畫訂單時,這顯然距他的理想很遙遠,雖不情願而又不能拒絕,難免暗生羞慚之心。更重要的是在日益商業化的市場環境下,帶有民間意味工筆寫真繪畫已經很難在市場上引起強大的視覺沖擊。他以個性鮮明的前輩繪畫為中心展開學習,從八大、石濤到“揚州八怪”,目的不是從他們身上學習古典雅緻的程式,而是尋求形式簡化和繪畫“書寫性”的啟發。相比之下,他更關心怎樣的書寫能夠幫助他直接達到這種效果,雖然金農和鄭闆橋的書法成為首選,但最理想的則是自己的“創造”。把何紹基與李邕的作為學習對象則更多與當時的環境相關。齊白石早年的日常書寫并沒有在19世紀前輩文人中脫穎而出,變革的迫切性如同繪畫一樣是當務之急。
當書法成為繪畫的依附,實用性的書寫則更顯得次要。是以畫稿中的書寫往往與繪畫之間沒有明确的界線。中國美術館所藏《蓮蓬蜻蜓》圖,主體是畫面左側長長的蓮竿撐起一支向右上角歪斜的蓮蓬,另一支從左下向右上斜出。一長一短交叉在畫面左下,單純的元素構成了奇崛的畫面,中段較工緻的蜻蜓頓時讓這近乎幾何化的空間生意盎然。站在書法的角度看,一米多長的蓮竿從中段開始用筆便略顯拖沓,渾樸無飾,中段因停頓而形成的“鶴膝”無法掩蓋揮寫這樣一條長線時的力所不及。第二條短線平鋪直叙,筆絲平行排列,沒有任何複雜的動作,線條力量在起筆處已經消耗殆盡。但這種線條卻在八大山人的某些作品裡已十分常見,經驗豐富的齊白石,在這一線條的末端用精緻的“白石體”款字作為收束,一收一放間渾然天成。僅有掌心大小的《蓮蓬蜻蜓畫稿》(圖16)所展示的是這種圖式的宿構,是稿作于1925年,整體無意為之而用筆渾重,“乙醜造稿”四字一意貫之,豪無修飾的線條在力量上卻遠勝于正稿。“乙醜造稿”不過随手記下,結字如常,用筆也談不上精到。書寫的連貫軸線依然可從斷裂的筆畫中清晰感受,“稿”字尤其如此。書寫狀态及線型變化與畫稿中勾勒蓮子的線條并無二緻。作為齊白石創作時以資借鑒的稿本,刻意于圖形标準化的設計,書寫的精粗并不在考慮之中,常常因繪畫的慣性而成。作于1934年的《墨荷蜻蜓圖》與這張小稿同屬一個圖式而略有改易,兩件作品勾勒蓮子所使用的線條依然保持一緻,而《墨荷蜻蜓圖》的落款卻和畫稿中的書寫有着天壤之别。
齊白石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對金農的書畫下過一番苦工。1926年樊增祥為《借山吟館詩草》作序時認為齊白石堪為“壽門嫡派”,不僅“書畫皆力追冬心”,作詩也實出金氏。1917年前後,齊白石書法處在放棄學何紹基體轉而學金農及李邕的階段。《勾臨金冬心賞梅圖》(圖17)是齊白石勾摹金農繪畫的草稿之一。通過對細節的觀察,齊氏學習古人的獨特方式深受金農的啟發,金農書法風格也被齊白石大量運用到創作及日常書寫中。此圖對落款的臨摹似乎并未熟練掌握金農書法的特點,下筆很不肯定,形體也不甚準确。勾摹稿在金農原款後補寫了“于揚州客舍”五字。将勾摹稿與原作對比,長寬比明顯不同,如果能夠排除勾摹所據另有他本的可能,便可以推測,在其徒手勾勒過程中,因起始部分位置的變化而導緻整體布局的移易使畫面變得擁擠。落款的空間變寬,左側留出多餘的空白,隻有增加款字填補空白,才能獲得與原畫一緻的平衡感。即使如此,畫面左端依然太空,便用行書注明勾摹時間,無意間的“補救措施”正是書寫作為附屬和補充物的展現。另一張《勾臨金冬心風來圖》與金農《雜畫冊》之三一緻。畫面比例有所改變,款字中有兩處變化,一是“面”字的寫法的改變,再是“壽道人”寫成“壽道士”。齊白石這些勾臨,最大的功能在于給繪畫創作以借鑒,對于圖式的把握重于文字内容及部分細節。從這一系列的勾摹稿看來,他的臨摹重點确實是畫面的形式,對于款字的準确與否并不關心,都是用自己的習慣做出記錄而已。金農《雜畫冊》之五,畫三五煙樹,朦胧中一農夫策杖期間,随意點染卻契合詩題“浮萍剛得雨吹散,吐出月痕如破環”。也許齊白石覺得隻有“雨”而沒有“月”的景緻并不符合自己的了解,故在上端增加山脊,又添一彎月,使畫面與詩意形成更加具體的呼應。落款的臨寫隻有細微的變化,開始随意不拘,寫到“稽留山民”時漸漸回到金農的筆調。這樣一來,意境似乎并無變化,水墨表現也遜一籌。他隻需借助一個基本架構為自己的創作提供參考,一目了然的構圖習慣成為他與前輩們區分開的一個标志,在他的畫稿中的确很少看到對模拟對象的“忠實”再現。他善于把圖像、文本和書寫重新熔冶到自主的創作原則中,從不因程式而感到掣肘。有時,這種變通的辦法确實為商業化繪畫的創作減省了負擔,即可以穩定把握作品品質,同時可以保證時間不被浪費,這無疑是齊白石處理這類問題常用的辦法。
齊白石繪畫的個體性集中表現在對母題的類型化,大量關注社會生活的題材,使他的藝術創作與社會之間的共存性得以展現,把文人畫的抒情性特征消解在戲劇化的日常生活中,畫稿中的書寫便成為強調戲劇化效果有效的說明。遊戲式的書寫所關注的并非書寫品質或風格類型,而在于是否達到了诠釋的效果。在齊白石心裡,畫稿也不是僅供自己檢視和使用的私密性檔案,他雖然反複說明它們作為“自家藏稿”的屬性。但對“制作”畫稿的得失,沒有象對待書寫一樣有着超然的心态,因為他一定知道這些畫稿終有一日會展示在更多人面前。就像他創作作品并認真署款時,态度便立刻端正嚴謹,使用最為熟悉可靠的書體,努力與畫面謀求一緻。他的大多信劄都給人展示出較好的狀态,而日常性書寫的直接性卻受到極大的抑制,大量精神世界的資訊被帶有修辭性色彩的書寫所掩蓋。長期應付不同場合及需求的書寫經驗,積累成穩定的應對機制,使創作與自由的日常性書寫判若雲泥。但是,在他畫稿中并不都是直接性的書寫,本文涉及的隻是普遍的現象。
圖18 《追摹八大小鴨》
圖19 《蚱蜢》畫稿
圖20 畫貓稿
圖21 樓蘭殘紙
圖22 簡牍
四、“一揮便了忘工粗”
唐代張懷瓘《書斷》曾有“心不能授之于手,手不能受之于心”的感慨,心手雙暢一直都被視為書寫的理想狀态。不知從何時起,書寫者的審美自覺意識就使書寫不同程度地受到制約,制約的因素包括“法度”、内容、情境及材料等等。長期從事書寫訓練的書家群體,或許都有一種追求:既能超越種種障礙而又能保證自然輕松的高品質書寫。在現實中的書寫實踐,往往很難兼顧兩者,或者不再謹守“法度”,稍加變異成為具有獨特性的書寫;抑或謹慎遵守筆筆有來處的箴規,小心翼翼地書寫,全然将自身隔絕在外。在齊白石日常的手稿中,書寫的前精後粗現象普遍存在。
作于1935年的《追摹八大小鴨》(圖18)畫稿有兩段款識,上端字多而謹細,右下角字少而草率随意,全用破筆散鋒,從風格來看當是同時書寫的,内容上看來是作為正文的補充。長款雖精工但還是難免前後精粗有别,逐漸放松甚至出現錯漏字。前文談到的《蚱蜢》(圖19)畫稿左側也有三行于1937年補作的題記,簡述了畫稿的由來。書寫時,筆鋒從始至終岔開,起收痕迹自然外露,毫不斤斤于筆畫得失,不過睹物思人,是以“太息”補記。題記的風格和同時期題畫詩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但精粗有别。典型的行書風格被儲存在“餘遊成都,白雲”數字中,但“色筆”以下的文字卻逐漸變成毫不在意的書寫,結字的平淡随意,用筆的簡率不堪替代了首行中類似“創作”的狀态,此間差異一目了然。
1939年,遠在桂林的徐悲鴻寫信索求齊白石“精品畫作”,“知己”雅囑不敢怠慢。齊白石自稱閉門數日,“蓄其精神”,畫了很多卻沒有自信可以拿得出手的,最後隻好以畫貓的舊稿作為底本,畫好寄給徐悲鴻。(圖20)嗣後在張舊稿上随手作了一段跋語:
前年為貓寫照,自存之。至己卯,悲鴻先生以書求予精品畫作,餘無法為報,(隻好檢此)隻好閉門。越數日,蓄其精神,畫成數幅,無一自信者。太息曰:作詩欲學李義山,每作一詩,搜書翻典,書堆左右如獺祭,詩成,或可觀,詩非不能也。維有作畫,有心為好,反腹手拙,若不偷竊前人,要于紙上求一筆可觀者,實不能也。(隻好)撿得此幅以寄悲鴻。(注:括号中字被圈去)
畫稿尺寸縱18.5厘米,橫30.5厘米,畫貓的空間已經去了大半,在剩下的空白寫下近150字顯然十分擁擠。原本打算寫三五行即可,“無法為報”後即接“隻好檢此”,文意至此基本接近尾聲。可是一貫講求修辭的他因偶然的觸動,決定寫下更重要的内容,于是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短文。跋文本身的意蘊暫且不論,回到畫稿的書寫上來,前三行字稍大,用的是常見于畫作上的風格。圈去“隻好檢此”後意識到空間不足,不得已把字縮小,變為前兩行的一半大小,單從書寫本身來看,水準相差很大,很不講究。小字前兩行依然謹慎地保持正常的書寫感覺,隻是因字小而稍顯粗率。從第三行開始塗改漸多,思緒被文意所牽,遣辭造句之際已經無法關注到書寫,謹慎的态度至此松懈,書寫的自覺意識無意間煙消雲散,剩下不計工拙的墨線縱橫交錯,識讀的功能一直保持。最後又在左上角用餘墨寫下“臨寄時,予存此稿”,書寫連綿婉轉,狀态稍複正常。整體看來,畫面的空白與雜亂的文字形成鮮明對比,隐隐感覺到書寫者飽含情緒的筆尖在紙面不斷翻騰。這種效果不是刻意制造的結果,而是因為自覺意識的松懈:審美自覺意識在他心裡占據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當每一次正式的書寫,都謹守原則而又傾力于自然揮運;如果書寫不再為審美或他人服務,這種謹慎的态度會頓時松懈,卻又并不徹底。書寫者自我揮運的自由往往受限于長期訓練中對範式的模拟,但除此又别無他途。隻有完全不顧書寫品質及視覺效果,才可能毫無顧忌地下筆,進而獲得書寫的自由。即使是王羲之、顔真卿以及宋四家這樣的名家,也很難在日常的書寫中避免因松懈或注意力的轉移而導緻相關的變化。即使在看似規矩嚴整的唐代楷書碑刻中也難免出現。閱讀齊白石大量的書信可以得到一個印證:這些為日常生活而服務的書寫,也大多受到主觀審美意識的操控,表現出前後如一、精謹的狀态。即使偶然寫到中段稍稍出現松懈,也會敏銳發現并立刻調整,這樣反而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視覺效果。這種效果的出現并非有意設計,“奇異”與“跌宕”往往與潛在的整體意識相關。
類似的複雜狀态在齊白石另一張《螳螂畫稿》中完整呈現,殘破的紙片上勾畫了四隻完整的螳螂。它們姿态各異,一隻羽翼未成,另有兩隻僅畫了頭頸部而被圈除。同在畫稿的是三朵萱花,一為雙鈎填色,一為白描,還有一朵沒骨畫出。不同角度和生長形态加上三種畫法的兼具,足以作為齊白石相關創作的重要依據。他一貫重視在現實生活中尋找鮮活的題材,認為依賴前人的陳法表現沒有見過的東西尚可原諒,若是目所能及的景物卻還依賴程式的話,無疑是愚蠢的做法。不落前人窠臼,是他自我意識形成中重要的觀念,仔細揣摩現實中可以表現的母體,并把它們進行高度概括和标準化。這時,畫稿的功能必須是可以滿足具體可用的要求的,任何一點線索都成為形成獨立表現方式的契機。除勾勒與敷彩外,唯有借助文字而得以盡可能的準确說明。該畫稿右側的題記從風格形式來看,一類屬于正常的帶有自覺意識的書寫,另一類則是較為随意的書寫。同一方寸之間出現兩種甚至更多種類的書寫形态,在齊白石畫稿中并不奇怪。再從内容來看,共分六組,其中五組是關于花頭的寫生,隻有“此四字言蟲”是關于螳螂的說明。有趣的是,這一組是後補在“寫意者好”之後的,且用波浪細線與下方劃開。原本是用來描述花頭,然而寫完螳螂之後卻借用來說明“蟲”,這當然隻是想更清晰地說明題記的所指,以便将來翻閱。但畫稿中書寫與繪畫的時間軸變得十分複雜,卻有利于我們分析其書寫心态的交替原則。“寫意者好”、“萱花側式”兩組點畫精到,以接近李邕的風格完成了較高品質的書寫,與其他幾組的率意随性形成巨大落差。這種落差在其繪畫作品正式的題跋中确實很少見到,但在畫稿與日記中俯拾皆是,不可勝數。1922年春,在東京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上,陳師曾為齊白石賣出一幅《桃花塢圖》,賣得“日金四百元”。後專為此作詩一首,字裡行間略帶欣慰與自足:
咫尺天涯幾筆塗,一揮便了忘工粗。
荒山冷雨何人買,寄與東京士大夫。
他對“一揮便了”的繪畫方式十分自信,不計工粗的繪畫狀态作為他獨特的标志而得到國際同仁的認可,他的苦心經營獲得了成功,雖然真正意義上的不計工粗隻保留在部分日常書寫中。遠在漢魏時代,也有這樣一批書寫者,他們以竹木簡牍為材料,日夜以抄錄為工作,在一些木牍和殘紙上也同樣呈現前精後粗的書寫狀态。如果将齊白石《蚱蜢》畫稿(見圖19)和斯坦因1906年在樓蘭遺址發現的信件殘本(編号為L.A.VI.II066)并置,(圖21)或把齊白石日記中的一些段落與出土文書殘紙相較,它們之間同樣存在前精後粗的書寫狀态,甚至連一些筆觸的形狀都十分接近。單純的書寫動作下所形成的線型具有共同的特性,這或許可以作為判斷日常書寫不同層次的一個名額。
具體的層次差異在簡牍書寫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執行個體。簡牍曾長時間作為書寫材料,它的寬度限制使書寫者的筆勢形成向下運動的習慣,當人們開始面臨同一平面内的多行書寫時,行與行之間的關系成為需要考慮的新問題,很多時候令人措手不及。(圖22)到齊白石的時代大幅面材料的适應問題早已解決,但處理多行之間互相關系卻是曆史遺留問題。人們經過反複的訓練習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處理方法,大多數時候都依靠慣性準确安排,但很難說清楚“安排”的程度到底有多少。另一種可能,當遇到書寫面變小,書寫者就得使用另一種經驗來做出調整。居延漢簡中早有這樣一種現象,在一方封緘上書寫有小字四行,按次第逐漸縮小,到最後一行時已經由隸書變為行草風格,沒有刻意規劃的書寫往往出人意料。相同
情況的不斷發生使得它們與正式的簡牍書寫區分開來,兩種書寫狀态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在毫無預計的前提下我們都很難保證自己的書寫品質,作為日常書寫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在齊白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一揮便了忘工粗”是齊白石長期在書寫、繪畫實踐和生活的互動中形成的觀念,他帶着這種觀念,沖破文人畫的形式慣例,為現代水墨畫創作開辟了新路。
五、結 語
長期的書寫積累不可避免習慣性偏好的産生,即使完全不關心書寫品質的一位普通書寫者,在經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書寫積累後,也會從中獲得便利、美觀的書寫經驗。但是,一般的書寫者多不願在書寫品質問題上耽誤時間,“美觀”與否不過餘事而已。當“餘事”為部分書寫者密切關注,甚至以此謀生時,“美觀”與否便成為重要标準。每當提筆之際浮現在腦海的,是前人那些精彩的書寫遺迹,它既是自如揮運的可靠依傍,更是一團揮之不去的陰雲。齊白石不甘在這團陰雲中盤旋,即使他的大半生都在竭力地靠近它。他所欣賞的有創造性的前輩藝術家給了他一個重要啟示:必須在格式的籠罩中脫穎而出。他不願意成為毫無新意的假古董,也從不非望“文人畫家”的稱謂。是以,很快從模仿古人的狀态中解放出來,大量的應酬更使他的日常性書寫與自身動作習慣相契如一。在熟練掌握何紹基、金農的書體之後,又在一股學習李邕的流風中,接納了向右上攲斜的字勢,并成為他書寫中最基本的風格形态。作為他所仰慕的前輩,吳昌碩的書寫也有着類似的特征,這種獨特在當時的國際市場備受青睐,這足以讓齊白石堅信這種形式的可靠性。從此,他再也沒有輕易改變過書寫風格,隻是不斷的在細節上作出微調,無論日常性書寫還是創作。
齊白石晚年極力提倡自由揮灑的書寫性繪畫,自稱“衰年變法”。大量生活化的母題在其創作中反複出現,一稿多用的創作方式,成為應對市場需求的一種政策。政策的背後,是某種書寫、繪畫方式習慣性的不斷延續。他像石濤、金農等前輩藝術家一樣,精心創造出屬于自家的畫稿。這些畫稿必須盡量準确地表達創造之際的想法,作為輔助的書寫與畫稿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這類書寫活動像日常生活一樣,按照本能的高度熟悉性正常進行。不需要嚴謹缜密的思索也能夠得心應手地完成,正因為它的得心應手,常被人視為平常無奇而不甚關心。在創作和日常性書寫長期交替中,高度重複性使日常性書寫在創作中能夠得到回報;而作為“本能”的日常性書寫又不斷向已有的實踐(模拟對象)經驗汲取營養,二者長期的互動,促使它們共同作出調适,形成内在統一的書寫機制。當生活和書寫分離之時,創作和日常性書寫之間又呈現互不幹涉的現象,甚至直接把日常性書寫排擠出“書法”的行列。齊白石日常性書寫和創作的關系時而泾渭分明,時而又互相滲透,這與自覺意識介入書寫的不定性或許有直接的關聯。在存世的古代書法作品中,也同樣可以找到相關的印證:古代簡帛、殘紙的書寫可以證明,書寫中前後精粗不一的現象并非是齊白石的專利,這一日常性特征更是此類書寫的一種傳統,意識的松懈、空間的安排是他們同樣面臨的問題。後世,“作品”意識不斷強化,書寫者把書寫視為“作品”,謹慎的意識會不自覺地浮現,當書寫為“不重要”的事件服務時,便立刻松懈下來。這種特性在齊白石書寫中得以彰顯,其根本原因在于,對文本功能性的關注導緻書寫過程中自覺意識的逐漸減退。
在傳統的觀念裡,“率意”的日常性書寫,在整個書寫體系中處在最基礎層次而被分化出來,這類作品很難進入收藏家和品評家的視野。并不是所有古代書家都像顔真卿那樣,一件祭文草稿也能被完整地儲存并且倍受珍視。關于古代這類書寫的研究,資料并不充分。以緻長期以來,盛行以審美談書寫的風氣,展現在觀衆面前的也多是精意的書寫,人們也不再輕易發表日常而随意的書寫。基礎層次的書寫長期棄置在專業訓練之外,書法創作逐漸與日常生活分離。創作的狀态回報到基礎層次的日常性書寫中,往往短暫而難以持續,隻有刻意為之才能保證品質。而日常性的習慣卻又要在創作中極力克制,即使偶然暴露,也會設法掩藏。往來之中,形成有趣的互動,也成為齊白石整個書寫系統的一個重要的特征。他在整理日記并寫下題跋時,總是顧慮文詞是否通亨和錯漏,從不涉及書寫的精粗問題,因為他從未把這類書寫當成書家之事。
齊白石日記、雜稿中所呈現的複雜情況與書寫風格的不斷變化,和不同階段的情緒、生活狀态相呼應。在日複一日的書寫中,他那精意的書寫逐漸變得随意輕松,從不斷改換模拟對象到穩定的習慣性書寫,極大的發展了自我意識。出入古人之際,不曾有一刻忘記“自家”,定居北京以後,尤其如此。他筆下那些顯得粗率不工的書寫,或許正為我們展示了書寫的本質:以傳遞語義為第一要務。再次從他的手稿聯想到顔真卿的《祭侄稿》,雖同是一氣呵成,但因“松懈”而導緻的粗率,成為齊白石書寫中可憾的缺失,他的得失為當下書法學習提供了可貴的啟示。本文在已有的相關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關注細節,期以細管而窺全豹,加深了對齊白石書寫問題的印象。叙述的同時,始終不敢稍忘美國學者喬納森 海的忠告:“天馬行空的論文不但不能加深對于齊白石的了解,反而有使這種了解變得支離破碎的危險。”
注釋略。
| 中國書畫推廣平台|
推介傳統經典之作、當代名家新作,
并以推廣新銳青年藝術家為己任。
| 策展 | 編輯 | 設計 | 出版 |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