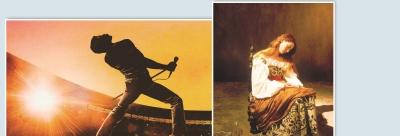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電影《卡拉瓦喬》劇照。制圖:李潔
《波西米亞狂想曲》在“偉大的音樂”和“争議的電影”之間,牽扯出的問題是,“拍藝術家的傳記片”和“藝術地拍傳記片”之間,怎樣握手言和。
如果沒有片尾20分鐘複制“皇後”樂隊在“拯救生命”演唱會的現場,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風評會打折。電影院變成卡拉OK廳,老炮們看了一遍又一遍,全場大合唱《我們是冠軍》,邊哭邊唱……見證電影有這樣的盛舉,主要功勞要歸給“皇後”樂隊,這是音樂的豐碑。
他看起來太正常,不太像藝術家
從弗萊迪·墨丘利留下的照片看,電影的男主角拉米·馬雷克和他差距挺遠的,他在表演層面的“好”,屬于電影的創造力,他用想象力賦予了一個角色骨血。裝了4顆龅牙的馬雷克一直看起來怯怯的,像隻受驚的倉鼠。弗萊迪本人那張臉欲望橫流,有種媚視煙行的妖冶,樂迷把他畫成一隻在聚光燈下光芒萬丈的搖滾貓,是有道理的。有資深樂迷撰寫長篇八卦,用學術的精神探讨《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劇情和現實細節的出入,一句話總結就是,這位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專業能力無可挑剔,但要說“弗萊迪靈魂附體”,就牽強了。
真實和虛構之間一定存在拉鋸,而“真實”并不是電影需要恪守的美德。《波西米亞狂想曲》在“偉大的音樂”和“争議的電影”之間,牽扯出的問題是,“拍藝術家的傳記片”和“藝術地拍傳記片”之間,怎樣握手言和。
《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兩個編劇,安東尼·麥卡騰寫過《至暗時刻》和《萬實體論》,皮特·摩根是《女王》《末代獨裁》和劇集《王冠》的作者。這個組合的共同點是擅長把傳奇的主角安置到普通人的位置,以普通人的局限去面對不普通的境遇,終于成就傳奇。這是“取觀衆最大公約數”的創作政策,“普通人性的不普通生長”,是親民的切題角度——看到權力漩渦或專業巅峰的人一樣受着塵世颠簸,妥帖誘導觀衆“想象代入”的立場。
用這個政策來寫“藝術家的傳記”,其實很大程度地回避了藝術的代價和藝術家的黑暗面。真實的弗萊迪放蕩不羁,他投奔了命運的深淵,留下的音樂給了普羅們遠方的憧憬,正因為這樣,他唱出“媽媽,人生才剛剛開始,我卻把它毀掉了”,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波西米亞狂想曲》創造出的一個“不挑戰普通人三觀”的弗萊迪,和這樣的歌詞、這樣的音樂也就沒太大關系。把藝術家聲色犬馬的冒險改編成私德有虧的“歧路”,讓他背負着忏悔“回歸”,這是一套戲台教化的說辭,把一個搖滾樂手塑造成一路逆襲的勵志者,他看起來太正常了,難免不太像藝術家。
有時候,藝術的撩撥力遠勝商業的精準算計
用虛構再現藝術家時,落點是“普通人”,還是取“藝術”這個關鍵詞,很多時候存在沖突,因為“藝術”往往意味着挑戰感。
導演賈曼拍畫家卡拉瓦喬的傳記片,電影由兩條平行的時間線拉開,一條是卡拉瓦喬在病床上垂死掙紮,另一條是他從少年時代起狂歡地活、狂歡地畫,把生命揮霍地投入情愛、鬥毆和創作。狂歡和垂死,這是卡拉瓦喬畫作的靈魂,對應着他的生命行歌。這電影裡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詞:藝術是生活的反面。賈曼大膽激越地拍出了藝術和生活的背道而馳,卡拉瓦喬絕望于現實的不藝術,他不能妥協,隻能在藝術的不現實中擁抱悲劇。這個劇作思路和核心題旨顯然不符合好萊塢統治的主流商業電影,但在1986年,它不僅獲了柏林電影節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也是那年英國票房最好的電影之一——有時候,藝術的撩撥力遠勝過商業資本的精準算計。
2009年法國凱撒獎最佳影片《花落花開》也是一部關于“藝術及其代價”的傳記片。德國收藏家威廉·伍德因為在一戰後發掘了畢加索和亨利·盧梭,名垂西方美術史,而在那之前,他還在法國鄉下發現了薩哈芬妮,一個粗俗的洗衣女工,她死在瘋人院裡,死後留名美術的萬神殿。《花落花開》的女主角就是薩哈芬妮,她看起來沒有一點兒藝術氣質,幾乎是有些愚昧的,但是當她從白天洗刷刷的鐘點工裡脫身,她在深夜裡畫出擁有熱切魂魄的樹木、花草和果實,畫畫讓她的靈魂掙脫出巴掌大的小村小鎮,通往神性的世界。法國外省的鄉村生活沒什麼波瀾,《花落花開》拍得也淡,就連伍德一次、兩次地背棄薩哈芬妮,也像風吹過樹梢,不落痕迹。這電影的法文原名是女主角的名字,中文片名的意譯很妙,藝術的誕生和藝術家的殒滅都如“花落花開”,是自然榮枯的傷逝過程,“天賦”這種東西,好像上天随意派發,又蠻不講理地收回,“天賦”的殘酷在于,要麼有,要麼零,沒有過程,隻有狀态。電影裡的薩哈芬妮說:“畫畫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愛。”這裡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同的方式”,就是藝術那根細細的紅線。
“藝術家的肖像”存在于一個微妙滑動的區間裡,他們不可能太“正常”,但也不是“不正常”的奇觀。在皮亞拉導演的《梵高》裡,梵高在生命的最後兩個月,受着精神疾病困擾,但他往返于聖雷米和阿爾勒的鄉間,吃飯,畫畫,愛,他謙卑地活着,不是聖徒也不是妖魔。朱麗葉·比諾什主演《1915的卡蜜兒》,離開羅丹的卡蜜兒是個受盡摧殘的女人,在修道院裡陷入谵妄的狀态,她是“閣樓上的瘋女人”,但“瘋癫”和疾病都是被建構的概念,是日常的瑣細把她卷入了内心的戰争。邁克·李導演《透納先生》,事無巨細地交代畫家的行動,在一段一段的人物關系裡交代他的自卑、他的粗魯、他的怪癖和他的驕傲。在這些傳記片裡,流水賬式的編年史和狹義的“戲劇”都被抛棄了,創作者讓“生活”,而不是“故事”,掌握着主動權,然後,傳記的主人公邁着日常的步伐進入了陌生地帶。
藝術地拍傳記片,就是為了趨近這片陌生地帶——“皇後”的音樂,莫紮特的歌劇,梵高和透納的畫,這些是塵世之上的一片飛地,藝術的靈韻在于奔湧的生命感,而不是靠流水賬的“憶往昔峥嵘歲月”,來妄圖得到一份心靈雞湯和生活哲理。
是以,《波西米亞狂想曲》裡浪子回頭的故事很快會泯然于衆多電影,而弗萊迪的歌穿越這個通俗故事繼續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