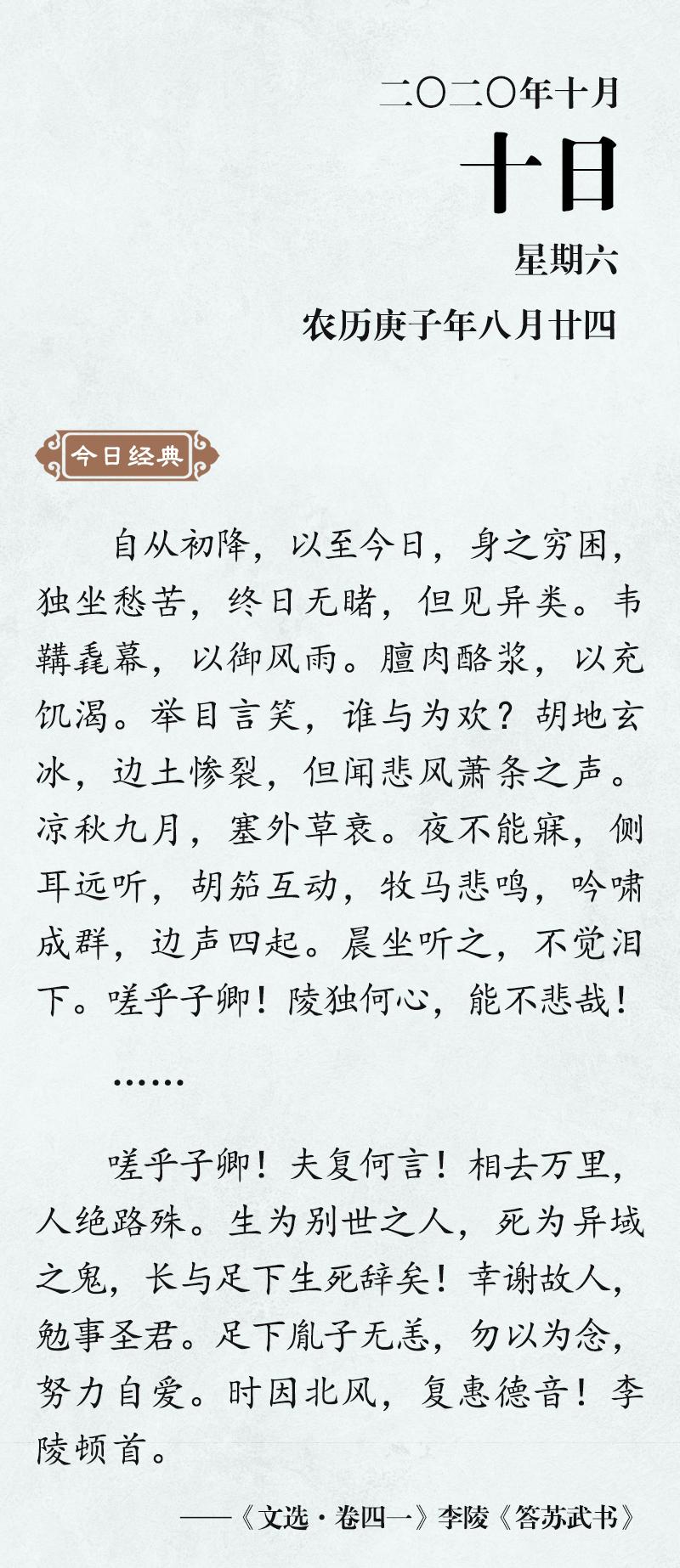
【譯文】
自從我投降匈奴至今,總是處于困頓之中,時時愁苦獨坐,整日難見一個故人,隻見異域風物。用皮衣、氈帳來抵禦風雨,用羊馬的肉和奶來充饑解渴。想舉目言歡,可有誰與語?塞外土地凍裂,冰層深厚,隻能聽見朔風凄厲悲涼之聲。到涼秋九月,塞草枯萎之時,我總是夜不能寐,側耳傾聽帳外的胡笳聲聲和牧馬悲吟,這聲音四處傳來,此起彼伏;或者在清晨聽這些邊塞之聲,不覺淚下沾衣。子卿啊!難道我的心能與衆不同,不以此為悲嗎?
……
子卿啊!我還能說什麼?這一别,我們相隔萬裡,往來阻絕,我活着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死後也是異域之鬼,确實是永遠地與您離别了!希望您回去之後代我向故友緻意,努力侍奉明君。您的孩子很好,不要太牽挂。請務必多多保重!也希望您能時常借北來之風,多多帶來好的消息。李陵頓首。
【小識】
李陵是李廣長孫,漢武帝時出身隴西的傑出将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因兵敗于浚稽山(今蒙古國境内)而投降匈奴。漢武帝得知李陵投降且為匈奴練兵之後,族沒李陵全家,一代将門隴西李氏就此沒落。
蘇武與李陵同朝任職,關系友好。天漢元年,蘇武作為使者被匈奴扣留,但他堅持氣節,始終不降,最終被迫于北海(今貝加爾湖)之畔,仗節牧羊十九年,“節旄盡落”,但仍然“卧起操持”,可謂“白發丹心盡漢臣”。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終得傳回長安。臨别前,李陵為蘇武置酒踐行,長歌當哭;傳回後,蘇武仍然寫信勸李陵回國,李陵便寫了這封回信。
在信中,李陵表達了他在漠北苦寒之地的孤獨與凄苦,以及對故土的深切眷戀;同時他也滿腹牢騷,對其轉戰絕域的艱辛與悲壯念念有詞,對自己投降匈奴的苦衷反複申述,尤其是對漢武帝族沒其家耿耿于懷,憤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着極強的感染力。應該說,若非知心朋友,若非毫無顧忌,是說不出這樣的話的。而李陵與蘇武,恰好交誼深厚,且李陵遠在匈奴,是以才能如此放言無忌。
另一個資訊是,在蘇武剛剛回國,尚未發出這封信之前,大将軍霍光派遣隴西任立政等人前往匈奴,以朝廷的名義召李陵回國,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為由,拒絕召回。可以肯定,這次征召,蘇武起了關鍵作用,他傳回長安後,為李陵說好話,才會引起霍光等人的好感。否則,漢朝投降匈奴者極多,而朝廷派人征召的僅有李陵一人,就很難了解了。
蘇、李兩人的經曆具有極強的傳奇色彩。李陵作為一代名将而身負國恨家仇,有“國士之風”卻最終成了曆史上的背叛降将;蘇武牧羊于無人的苦寒之地十九年,曆盡辛酸,九死一生,傳回時已“須發皆白”;而且二人又都出身世家,交情笃厚,早先同朝任職,後來各為其主,其漠北訣别、絕域鴻雁,無不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應該說,是特殊的出身和境遇造就了蘇、李二人獨特的個性魅力,也賦予了他們真摯言情的文學才華,進而成就了曆史上最早也最典型的知己長别。是以,李陵、蘇武就成了後世文人渲染離别之悲的典型題材,他們間的臨别之歌、贈别之詩、往返書信,向來為人津津樂道,甚至多有懷疑之詞,認為這都是後人的僞作。我們以為那些懷疑都僅限于推測,并不确切,其作品多是其本人所寫,《文選》的選錄也算是一個側證。(蕭寒)
黃柏
黃柏:呈闆片狀或淺槽狀,長寬不一,厚3~6mm。外表面黃褐色或黃棕色,體輕,質硬,斷面纖維性,呈裂片狀分層,深黃色。氣微,味甚苦,嚼之有粘性。清熱燥濕,瀉火除蒸,解毒療瘡。用于濕熱瀉痢,黃疸,帶下,熱淋,腳氣,骨蒸勞熱,盜汗,遺精,瘡瘍腫毒,濕疹瘙癢。主産于四川、重慶、貴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