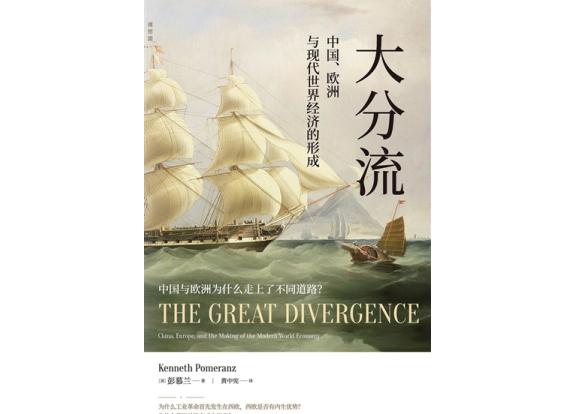
《大論壇報》,彭木蘭著,黃忠賢譯,理想國度,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4月。
大轉移書:什麼是"大轉移"
"大鴻溝"回應了經濟史上最經典的問題之一,即為什麼西歐是世界上第一個向現代經濟增長模式過渡的地區,而中國曾經與之相似,但自18世紀以來卻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澄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在近代,中國和西歐都處于發展的形勢。
彭木蘭在本書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呈現的是一幅大多數學者都不敢相信的圖景:直到1750年,東亞和西歐,或者更具體地說,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與西歐最發達的英格蘭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在人口、資本積累、資本積累、人口、 技術,土地和要素市場以及家庭決策。當視角轉向奢侈品消費和"資本主義"制度時,彭木蘭發現東西方之間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都不足以産生中西之間的轉移。特别是,中國(和日本)和西歐等核心地區在生态限制程度方面的壓力幾乎相同。
是以,《大分流》的第三部分解釋了中西分流的主要因素。彭木蘭認為,19世紀歐洲從舊大陸轉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煤炭資源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新大陸的發現。兩者都使歐洲集中使用土地變得不那麼重要,同時在其資源密集型産業中創造了增長。全球形勢使美洲成為歐洲所需的初級商品的主要來源,大大緩解了歐洲的生态限制。這種運氣使歐洲能夠轉向資源密集型、節省勞動力的道路。與此同時,亞洲已經陷入了發展的死胡同,沿着以前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節約型的道路越走越遠。
對于西方學者來說,這本書和許多加州學者(如王斌的《變形的中國》、李忠清、王峰的《人類的四分之一》)一樣,打破了曾經流行的"震撼反應"模式和歐洲中心主義,讓他們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曆史的發展。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迪爾德雷·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這樣評價這本書:"帕梅拉利用歐洲的發明,經濟學,推翻了歐洲的中心主義......歐洲人将不再認為,從曆史上看,他們是唯一站在經濟增長之門前的人......"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這是一本開創性的書。《大分流》的偉大貢獻之一是指出了互動式比較的重要性。正如彭木蘭所說,"...諸如"為什麼英格蘭沒有成為江南"這樣聽起來很奇怪的問題當然不會比更習慣的"為什麼沒有成為英格蘭"更好,但它們并不遜色,而且它們具有重要的優勢。"我們不應該以江南或英國的任何一部分為标準,也不應該忽視前工業社會發展中的任何普遍或具體的東西。
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國經濟史領域,學者們就明清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為什麼中國在其曆史上"失敗"——未能成為第一個經曆工業革命的國家——進行了辯論。這本書無疑讓學者們意識到,現代經濟增長可以采取多種形式。
然而,盡管《大轉移》一書為學術界了解大轉移問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并非沒有缺點。本書中的大部分證據來自二手文獻,而不是材料。這樣做會在列出的證據中産生選擇性偏見,即作者隻能提出有利于他們觀點的證據,而忽略文獻中涉及的其他不利證據。
圖為清人虛谷作品《小橋流圖》,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經濟社會中人們更向往的生活場景。
從"大轉移"到去:何時以及如何"大轉移"
在《大轉移》出版二十年後,關于大轉移的讨論從未停止過。2002年5月号的《亞洲研究雜志》刊登了《大論壇報》的四篇評論文章,包括黃宗志的書評、彭木蘭對黃宗志的回應、李仲青、康文林和王峰對黃宗志的回應(筆木蘭在他的書中對中國模式的證據主要來自李、康、王的研究),以及羅伯特·布倫納和克裡斯托弗·伊塞特的評論。其中最著名的是黃宗志首次讨論中國的增長是發展還是内部體積。
黃先生認為,彭先生在書中對江南先生的描述過于樂觀,英國過于悲觀。他認為,該書将18世紀及以往英國經曆的五大革命發展,包括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市發展、人口轉型和消費變化,解釋為内部體積(指機關勞動邊際報酬的下降),以及18世紀江南在人與土地沖突日益加劇下産生的内部體積增長。 發展變化,進而使兩個地方的發展模式在1750年左右非常相似。他還指出,這本書側重于用數字來衡量增長和發展,忽視了實地的真實情況。
然而,自黃宗志以來,對農業重大轉移的研究較少。在他們最新的研究中,馬雲和彭先生指出,農業本應是轉移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但十年來,學者們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是以,他們從農業生産的角度回應了大量轉移的問題,建議在中國增長的形式中考慮季節性因素,特别是季節性對中國農業與手工業互相作用的影響。正如Ester Boserup的理論所表明的那樣,人口增長增加了土地耕作的頻率,并促進了勞動力使用技術的創新,使農業"集約化"。同時,前工業化時代中國經濟明顯的季節性特征,使勞動力從農業轉向手工業等副業,增加工作日數,最終增加年收入。他們的新研究無疑為學者們提供了内化、工業化、現代化的新視角。
除了關于江南18世紀發展模式是内部還是發展的論述外,學術界對大轉移問題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即大轉移的時間和大轉移的原因。
大轉移表明,在1750年之前,東亞(以中國和日本為代表)和西歐具有相似的經濟發展路徑,而兩地之間的轉移發生在18世紀後期。彭先生後來修改了他的觀點,認為轉移發生在18世紀中葉左右。這本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糾正以前認為是非常早期的轉移,正如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在公元1000年和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ison)在14世紀所認為的那樣。
近年來最轟動的文章之一是Stephen Broadberry,Guan Hanxuan和Li Daokui,發表在《經濟史雜志》2018年第4期《中國和歐洲長期GDP會計研究》上。他們發現,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轉移比加利福尼亞學派認為的要早,但也比歐洲學者認為的要早。根據他們的統計,中國的GDP在1700年約占英國GDP的70%,1750年為44%,到1850年已降至20%。即使将江南與西歐發達國家進行比較,GDP的差距在1720年左右也開始擴大。
對于大轉移的原因,近二十年來,學者們從制度、文化、人口、技術、産業結構、貿易、國家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總的來說,更多的學者在解釋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時,更關注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例如,黃宗志認為,英國早先描述的五次革命變化是根本性的前提,而中國(或江南)在18世紀沒有革命變化。趙定新指出,彭木蘭的分析缺乏對中國和西方制度因素的比較,他認為,中國富裕地區和西歐較發達地區的生活水準在明清時期是可比的,當時中國技術創新的低回報率和儒家思想的實力在19世紀左右無法在中國取得任何根本性的突破。
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的《現代英國工業革命的啟示——對世界的深刻視角》(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強調了英國高工資模式和低能源(煤炭)價格對工業革命的重要性。這兩者也與英國城市擴張、貿易增長、農業進步和人力資本增加的轉變密切相關。明清時期中國的低工資模式和高能源價格使發展道路與英國不同。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最新研究也延續了他長期以來的觀點,即西歐文化與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國文化不同,因為它不同于西歐文化中的懷疑,開放和好奇心。這三個品質使西歐文化更容易創造和吸收"有用知識",促進西歐科技的發展,進而使西歐走上工業化的道路。
然而,在後來對大轉移争議的回應中,彭先生指出,他并不認為導緻轉移的因素,如制度變革或技術創造和改進,并不重要,而是煤炭和新世界的重要性被學術界低估了,并希望他的研究能夠導緻對曆史偶然性的更深入了解。真相越清楚,這些争議越是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界對大轉移問題的認識,其實這也是研究的方式,正如彭木蘭在采訪中所說(參見陳黃軒的《全球曆史視角下的中國曆史——彭木蘭教授訪談錄》、《曆史理論研究》2017年第1期)所說: "面對一些宏大的曆史問題,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拿出一個完全正确的解釋。"在不斷的辯論中,真正的經濟史總有一天會恢複。
作者|哈瑟
編輯|羅登
校對|于永軍